关键词:钱钟书;纯文学;准文学;时间意识;强制阐释;不即不离;整体性
内容提要:钱钟书从“诗象”与“易象”的比较出发,对纯文学作品与准文学作品之间的亲缘关系与本质性区分进行了创造性的论述。本文认为,必须经由审美活动作为时间意识或时间视域如何构成及审美对象之空间构成特性的角度,才能凸显这一思想的创造性及弥补其隐而不发的遗憾,并修正其过于偏向或者孤立地论述审美对象构成而不是审美活动构成的倾向。钱钟书认为,上述两者作为意向活动与具体作品语言构成之间是“不即”与“不离”的关系,即纯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仅仅体现在——奠基于特定语言空间构成之上的时间意识或时间视域,其语言的空间构成或者位置绝不可以做任何改动,整体性要求最高;而准文学作品语言的空间构成则可以改动、替换、更张,却不影响其目的与意蕴,整体性要求不高。钱钟书在此思想基础上阐明了两者之间存在的互相僭越、强制阐释的可能性、机制及其规避策略。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象学美学中的时间性思想及其效应研究”(16BZW024)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8)06-0125-06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8.06.018
文艺理论知识体系的逻辑出发点是确立研究对象及其价值,继而所产生的问题必然是:对象的呈现状态如何?是如何构成的?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清晰的、自明性的描述,各种价值就会混同起来,在各种价值活动的呈现状态及其基本构成方式之间也就会产生强行僭越,强制阐释就必然产生,那么,文艺理论的知识生产就无从合理地、合逻辑地展开。一个已经完成的文学阅读活动正是文艺理论唯一的、也是最高的研究对象,且其呈显的原初状态是:作为一种流畅的、时间视域性的愉悦感奠基于特定文学作品固定的空间构成关系。
强制阐释的核心在于以其他价值僭越、混淆、消解审美价值,而强制阐释的具体操作则在于无视、曲解或瓦解文艺欣赏活动作为流畅时间意识的空间构成。钱钟书反对强制阐释论的特别之处体现于——在审美价值与类审美价值或者纯文学作品与准文学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上展开视野。所谓“纯文学作品”指的是那些仅仅提供阅读的过程性愉悦并因而具有纯审美价值的作品,而“准文学作品”所指的是那些以阐发义理为根本目的、以阅读的过程性愉悦为手段并因而具有类审美价值的作品。他所批评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各种典型的强制阐释现象如“诗无通诂”“求女思贤”等等,力图守护纯文学作品阅读活动作为美感所具有的流畅的、兴发的时间性状态及其所奠基对象的固定空间性关系。从汉语美学角度而言,钱钟书的“不即不离”之论展现出以地道的汉语,甚至以古雅的汉语词汇来进行概念命名、命题、运思及与西方美学直接进行对话的自信及优长之处,因为中华美学精神最为辉煌与悠久的传统就是确保审美活动自身原发性状态的完整性。
一、审美活动作为时间意识的流畅性与空间构成的整体性
人们总是乐于追求持续性的、流畅的且状态极为纯粹,毫无迟滞、阻隔与断裂的愉悦感,也希望能够保存正在兴发着的各种经验与情致,这是所有人无须证明的天性。在人类的很多生活领域,还必须追求实践或者行为自身持续的流畅性,并力图保持其兴发性的状态。这一切,在审美活动或艺术欣赏活动中体现得极为显著,而这也正是时间感或者时间性最强的领域之一。
不同于科学活动、宗教活动所追求的无时间感、无时间性的纯粹客观之知识与纯粹主观之神灵,也不同于在数学—物理空间中呈现绝对匀速运动的“点状时间”,审美活动自身寻求并呈现为一种兴发着的、涌现着的、前牵后挂的“域状时间意识”“时间晕”或者“时间视域”;当我们阅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到“水”之时,此时的现在感最强(原印象),不过,前面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并没有消失,它们仍“滞留”于注意力的视域之中,但绝不是回忆,更不是反思性行为;且由“水”向前同样是一个生动的、兴发着的“前摄”(期待意向)有待被充实,这些字词作为素材或者材质在诗句中被立义为富有意蕴的审美愉悦行为。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人们就无法听到旋律,就不会唱歌,也就无法体味到那种充满“继续欲”或者“持续欲”、仿佛被拽着、被吸引着、被牵拉着一般持续向往、向前的美感。
由此生发且同样重要的命题是——审美意向行为作为时间视域或者时间意识,必定是由审美主体指向由具有特定空间性关系——诸如位置、结构或者方位的多个相位或者要素的审美对象所构成并显现出来的。当我们说自己从艺术作品获得了完善、完美的审美愉悦的时候,其实就同时可以转化为或者转训为另外两种陈述——
第一,这一艺术作品的诸要素之间在空间构成上是整体性的,艺术作品的所有要素都在整体之中发挥特定的作用与功能,这意味构成这一空间的所有要素从单体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且它们都处在特定的或者只能是固定的空间位置、方位之上。当然,在这里所说的空间,绝不是一个真实世界中的三维立体的客观空间,也不是几何学意义上的抽象空间,而是指构成一个文学作品的所有要素之间的位置、方位或者结构关系。这个空间、空间构成或者空间构成关系在任何一部作品当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或者任何一部作品的空间、空间构成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其中尤其以纯文学作品的空间构成整体性要求最高。
第二,这一审美活动作为兴发着的时间意识必定是流畅的域状物而不是点状物。事实上,当我们说一个作品是一个“整体”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描述对这一作品进行欣赏的审美活动的“流畅性”;反之亦然,且“流畅性”是最为根本的,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有可能对作品的空间构成的整体性进行判别、言说,因此,“流畅性”与“整体性”并不是一种等价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孜孜以求、流连于感觉及感官愉悦的丰富、流变、新异,这是一种主客不分离的悦乐文化,也是一种时间性极强的文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审美与道德领域之中的亲子之爱,尤其是亲子之爱中的“慈”更是人世间冲动最强烈、最自然、最超乎功利且绵延最久的美感。儒家的根本在于“仁”,其具体呈现为“礼”的行为,而“仁”的核心正是基于亲子之爱的“慈孝”之情。因此,中华美学精神既是一种执着于享受家庭幸福的文化,也是一种钟情于现世悦乐的此岸文化,尤其是当礼成为国家治理、社会管控、家庭秩序、个人修为的系统规范,且与乐、诗、文、舞等艺术等无间地合流之后,强大的礼乐教化传统就形成了。这就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家国情怀的具体内涵。可以说,中华美学精神与西方美学相比,它更完满地保全了审美活动构成的完整性,但是其主要弊端就在于——当礼教的国家需要、意识形态需要远远超出家庭之时,“国”就会僭越“家”,正如钱钟书所分析的,最为典型的体现就是自汉代以来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往往惯于把诗歌中的“男女”阐释为“君臣”,把“求女”说成是“思贤”,而且以此成为专门名家者甚众。除此之外,钱钟书还论及宗教(佛教)对于审美的强制阐释,他认为佛教的宗旨在乎“空”——即禁欲,也就是尽力避免感官愉悦的兴发与绵延,其所利用语言的目的正在于“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而文学的语言则是空间构成的整体性要求最高,他所维护的也是审美活动作为时间意识或者时间视域构成的空间完整性。
钱钟书对纯文学作品与准文学作品差异的比较的手眼与思想工艺极为独到,主要体现于对审美价值与类审美价值及呈显状态之间进行比较、辨识。他所撰《管锥编》《谈艺录》中的文章与《七缀集》中所列单篇长文不同,一般来说并不专门就某一学科中的某一问题进行专题而系统的探讨,尤其是《管锥编》就愈发依据对古代典籍、文集的阅读,凭依着自己的兴致,往往在某一细处展开论述,且文字一般极为短小精悍,惜墨如金,用典博雅,不过,仅仅就文艺理论、美学而论,钱钟书的这些细小之论却处处包蕴着精辟之见,且新意迭出,其眼界之遥、识力之深、创造性之巨都是出乎意料的。在篇幅、行文上的简短,只是印证着人生有涯、精力有限,钱钟书实在是无暇而不是无力扩展文字,把那些精致的、浓缩的、堪称核聚变一般的文字衍化为长篇大论。在以上两部巨著之中,有一篇文章却是例外,那就是《管锥编·第1卷》论及《周易正义》之“乾卦”篇。就此篇文章的整体而言,其核心内涵就是阐明“易之象”与“诗之象”的根本区别。简言之,如果把属于准文学的“易之象”等同于隶属于纯文学的“诗之象”,且把前者的价值及其呈现状态施之于后者,“强制阐释”就必然产生。
纯粹的审美价值所指的是审美对象仅仅能满足感官愉悦之用,虽然具有这种价值的艺术作品在内容、意蕴、题材上所表达的是现实、人生、事件、情绪,甚至很多艺术作品在意蕴、题材上的功利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很强,但是并不妨碍这些作品作为较为纯粹的审美价值而存在。当然,在此绝不能孤立地、抽象地谈论审美价值,而是就具体的审美活动的状态而言的,且只能如此。如果一个审美主体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只是沉浸于纯粹的、流畅的愉悦过程之中,只以此为乐,而不是把这个艺术作品作为一种为了他用的工具或者手段,这就是纯粹的审美价值及其活动。而不纯粹的审美价值所指的就是那些除了具备审美价值之外,还满足其他目的的审美对象,更准确地说,审美价值往往退居其后,成为一种手段与工具来完成其他目的,举凡以形象、生动的手段来阐述科学原理、宗教教义、道德规范、思想哲理等的艺术作品都是如此。
二、“不即”:准文学时间视域之空间构成的不固定性
钱钟书对纯文学与准文学的比较是从对《周易》与《诗经》的比较开始的,因为《周易》与《诗经》既在形象性、生动性上有相通、相似之处,又在传达、显现人类兴发性经验上骑驿相通、独树一帜。
以形象而生动的方式来显现道理是遍及古今中外的普遍现象,而且最为惯常性地使用的手段就是“比喻”,他说:“理赜义玄,说理陈义者取譬于近,假象于实,以为研几探微之津逮,释氏所谓权宜方便也。古今说理,比比皆然。”①在这段话里,钱钟书既指出了这一事实,又指出了通过形象性的语言与其所显现的道理之间并不是一种直接相等的关系,并不是道理自身,而只是一种“手段”而已。就相通之处来看,两者都会给人们带来愉悦的、生动的、形象的感受;就本质区别而言,纯文学作品给人带来的仅仅是过程性的审美愉悦,而准文学作品仅仅把由其所带来的过程性愉悦视为工具与手段,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所要阐明的义理甚至科学知识等等。
如果能够看到两者之间在价值上的根本差异,并能在这一前提下,根据上述审美活动作为兴发着的时间意识及其空间构成,对两者之间的意义生成机制或立义机制进行深入分析,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挑战。钱钟书回应这一挑战所要解决的是——以纯文学作品为对象的欣赏活动的构成方式及显现状态是什么?换言之,强制阐释造成的既是纯文学与准文学之间在时间意识及其在空间构成上的混淆,更造成了以上两种价值之间的互相强制阐释与互相僭越。如何才能不互相僭越?如何才能规避相互间的强制阐释?僭越与强制阐释就必定体现于审美活动作为时间意识构成的改变,也就是时间意识空间构成或者空间化的改变。要克服与应对强制阐释,就必须立足于审美活动上述构成方式,也就是立足于对确当阐释的正面且完整的描述与分析。本节所论的就是第一个僭越及其应对策略。
(一)准文学作品与类审美价值的存在状态
对于准文学作品来说,在审美与义理之间如何寻求一种平衡是极为关键的,既要首先确保义理的价值及其呈现状态的明晰,尤其是要确保其在人类理性交往公共平台上的正常沟通,也要维护来之不易的美感之翼,因为化抽象理性为生动直观的确是人类最可贵的天赋之一。
针对上节所述易象的“取譬”目的在于“明理”,钱钟书表达了戒备之心,他说:“古今说理,比比皆然。甚或张皇幽眇,云义理之博大创辟者每生于新喻妙譬,至以譬喻为致知之具,穷理之阶,其喧宾夺主耶?抑移地就矢也?”②在科学与哲学语言中常常充满了比喻性概念、术语以至于陈述的事实,隐喻或者比喻在科学著作中具有认知功能,在其运作中必须从审美功能转换至认知功能,由修辞的宽容转换至实在的严谨。因此,审美与修辞在科学著作、哲学著作中只是一种有待超越到、升华到或者转换到科学与哲学之思的“手段”与“工具”。否则,“工具性”就有可能僭越为“目的性”,也就是他所言“喧宾夺主”与“移地就矢”,他说:“《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语本《淮南子·说山训》)。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象,舍象也可。到岸舍筏、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谓也。”③在这段话里,钱钟书从两个方面指明了科学、哲学著作中“象”或者“比喻”的作用与功能:
从第一个方面——“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来看,也就是从科学著作、哲学著作的写作过程来看,以“A象”或“A比喻”乃至于“B、C象”或“B、C比喻”都可以说明、阐述同一个道理,把“A”变更为“B、C”等等语言、符号也是完全可以的,并不拘泥于“A”。这意味着以义理之趣为主的准文学作品在对语言、形象的选择上有较大的自由度,虽然也需要锤炼词句、精心构思。
从第二个方面——即“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来看,一旦科学、哲学著作写就,且对其阅读过程完成或业已领会了该著述中的道理之后,“象”“比喻”等形象、生动的手段或工具便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使命,在这个时候,读者的注意力就应该完全集中于“道理”之上,不再附着于、恋着于“象”或者“比喻”等语言、符号,以至于可以完全舍弃、忘记其存在。当然,这一道理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在一个具体的对准文学作品进行阅读的过程之中活生生地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读者会自觉地或者应该自觉地把构成准文学作品的比喻、形象等诸要素立义为“道理”或者“义理”,而且这一立义活动同样不是一个反思性的、在阅读之后再进行总结、归纳、推理的行为。这一阅读过程本身不仅是当下即席的,而且是一个流畅的、前牵后挂的视域性行为过程。
(二)准文学的“不即”特性与如何抵御以审美强制阐释义理
从审美价值对义理价值的不利影响来看,这一僭越体现在仅仅把注意力停留在审美性、修辞性的“象”“比喻”等工具性存在上,而忽略、忽视了这些工具与手段所要表达的“义理。正如王弼在论及易象的目的与如何把握易象、比喻时所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④钱钟书对此的总结是:“恐读《易》者之拘象而死在言下也。”⑤这一总结正是针对审美价值对认知价值可能发生的僭越或者强制阐释而言的。“健”之“义”不一定必须由“马”来体现,由“天”也可以体现;“顺”之“义”既可以由“牛”来体现,也可以由“羊”来呈显,钱钟书说:“象既不即,意无固必,以羊易牛,以凫当鹜,无不可耳。”⑥这意味着构成“易象”或者“准文学作品”诸要素及其空间构成的固定性、整体性程度不高,不仅这些要素、单子可以被更改,而且这些被更改之后的作品所得到的“意义”或者“道理”却没有改变,或者虽有美感、愉悦感的衰减、退化、衰退发生,但是“意义”或“道理”变化不大;甚至当这些空间构成要素变化极为剧烈,美感的衰退、退化、衰减程度极为夸张、极端,乃至美感、愉悦感全无,及至最终剩下来的只是干巴巴的、抽象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术语、概念及其逻辑性的推理、思辨的规范陈述,仍然还可以说是不至于伤筋动骨,因为“意义”“道理”“思想”等等还存在于此。
因此,准文学的意义与价值是为了阐明“义理”。在对一个文本进行阅读的过程中,如果审美愉悦与“义理”同时被立义,或者同时被显现出来,当然,这样两种因子是在“一个”阅读行为中复合性地同时呈现出来的,那么,如果“义理”居于上风,读者得到的就是一个以审美愉悦为辅、以“义理”为主的阅读体验,如同本文第一节所述,在此呈现的“义理”就会呈现出一种活生生的、兴发着的愉悦状态,读者就可以判定,此文本是一个准文学作品。
审美与修辞会给“义理”带来不便,最大的问题就是极具个性化、风格化或者诗意化的陈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个自足的独语,也就是说,比喻或者其他形象化陈述必须转换为、转渡为一般性的、可在纯粹逻辑知识平台上进行公共交流的术语、概念、陈述方式,并显然要自明性地具备含义的明晰与固定,才有可能成为义理或理论语言。因此,仅就《庄子》而论,其《逍遥游》一篇的主旨在于陈述这一道理——“一个人应该看透功名利禄,看破权势尊位,摆脱羁绊,使精神臻于自由自在的无碍之境”,在这句话中,“应该”“功名利禄”“自由自在”“无碍之境”“精神活动”等等就是上述可供公共交流与沟通的一般性的哲学术语、概念及命题,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拿“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南冥”等等作为一般性的、公共性的且高度明晰、内涵固定的术语与概念,来进行纯粹逻辑的交流与沟通。
为了应对准文学之中的审美与修辞对认知价值、义理的强制阐释,钱钟书还提到一些典型策略。针对佛教经书与《庄子》所大量运用的博喻修辞现象,他认为这可以有效地规避单一喻体可能造成的与本体混融不分的僭越现象。关于《庄子》,他说:“夫以词章之法科《庄子》,未始不可,然于庄子之用心未始有得也。说理明道而一意数喻者,所以防读者之囿于一喻而生执着也。星繁则月失明,连林则独树不奇,应接多则心眼活;纷至沓来,争妍竞秀,见异斯迁,因物以付,庶几过而勿留,运而无所积,流行而不滞,通多方而不守一隅矣。”⑦这种方式所起到的后果就是使读者在对准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中淡化本体与个别喻体之间的直接联系,甚至一定要拒斥在本体与单个喻体之间的直接等同,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或者使注意力分散地关注博喻中的每一个喻体,这就是准文学为了抵制审美、修辞或者比喻对义理、道理的强制阐释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之一。
三、“不离”:以纯文学作品的整体性抵御强制阐释
本节所论即产生强制阐释的第二种可能性,即把准文学作品空间构成上的不固定性强行施之于纯文学作品,这也是本文的重点与核心所在。
(一)“不离”:纯文学作品空间构成的整体性
与对准文学作品阅读中的“得意忘言”及时间视域空间构成上的不固定、可替换等整体性不强诸特性相比,对于纯文学作品来说则完全不同,钱钟书说:“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诗甚且非诗矣。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sign)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icon)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⑧可见,两者之间的差异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仅仅从字面上来看,钱钟书所使用的“舍象”“变象”“易言”“更张”与上节论及准文学时所使用的“舍其象”“变其象”“取代”一样,是侧重从构成纯文学作品的诸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或者空间性而言的,似乎钱钟书只是把纯文学作品当作了一个绝对自立、自足性的存在者,事实上,他是始终把审美活动或者文学阅读活动的意向性构成方式作为唯一的合理视野,且这一意向性活动最为原初、原生的存在状态就是一个一直向前涌现着、兴发着的且主客之间不分离的愉悦活动,因此,他所论纯文学作品或“词章”“诗象”绝不是一个抽象的、一般性的、普遍性的“定义”,也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时间性因素的、固定不变的“本质”,而是一个当下即席、随时机而兴发的且前牵后挂的视域性行为或者事件,比如在对《诗经》中的《车攻》等文本进行阅读的时候,纯粹的审美愉悦就会被触发、绵延,也就是被立义为一个以纯粹过程性的、视域性的愉悦作为目的与价值的审美行为或者事件,读者就会把这一文本称为“诗”“词章”或者纯文学作品。尤其是在论及对纯文学阅读过程中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是一种“不离”关系的时候,审美活动作为且只能作为意向性活动——审美主体始终指向审美对象的根本构成特性就愈发刺目地显现出来。当然,对于准文学的阅读活动本身也是一种意向性行为,钱钟书所做的,就是对这两种意向性行为从价值差异的角度进行时间视域的空间构成比较。
对于“词章”“诗象”或纯文学作品而言,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对于那些纯粹的以感官愉悦为目的且仅仅对愉悦之过程流连、徜徉的审美活动而言,其只能由特定的审美对象来奠基,只能由构成这一审美对象的诸要素之间独一无二的空间构成所奠基。当一个纯粹的审美活动作为一个时间意识或者时间视域正在兴发之时,正是审美主体的注意力贯注于构成审美对象的诸要素的空间位置、方位上的时候。正是构成审美对象诸要素之间的固定空间关系,才使得审美活动作为时间意识或者时间视域得以立义。正如本文在开头处所述,人们不仅几乎都具有把握连续性对象、意识、行为的能力,而且更孜孜以求愉悦感的纯粹、流畅、绵长、强烈,这正是一个由原印象、滞留、前摄不断流淌、涌现、后坠而形成的一个时间晕或者时间视域,也就是说,构成时间视域的原印象、滞留、前摄三者之间并不是现在、过去、将来的持续关系,而是在一个视域或者晕圈中的同时性存在,而绝对不是由一个点在某一空间中的匀速运动所测得的时间。就《诗经·车攻》之诗句——“马鸣萧萧”而言,“马”“鸣”“萧”“萧”在未被阅读之前,只是四个呈现前后排列的文字或者素材而已;在一个完美进行的阅读中,当注意力指向第三个字“萧”的时候,前面的“马”“鸣”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为视域中的滞留;且正在兴发之中的审美活动都会保有一种流畅的、持续、继续下去的欲望,虽然该句中的第四个字“萧”还未进入到视域之中,但是当注意力到达第三个字“萧”的时候,“前摄”已经作为一个有待充实的意向或者欲向出现了。因此,正是由于“马鸣萧萧”中的每一个字词都绝然固定且所有字词都处在独一无二的空间位置、方位抑或相位之上,对于它的阅读才会当下即席地被立义为一个纯粹的愉悦获得行为。
钱钟书在此流露的纯文学或者纯粹审美活动作为时间视域的思想具体表现在“时流之迹”或者时间视域之“迹”的论述上,且主要与对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汉语翻译及在此基础上的新开拓直接相关。钱钟书把sign翻译为“符”或者“符号”,而把icon翻译为“迹”——“《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sign)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icon)也”⑨,无疑更加准确、雅正、传神,尤其是就传神而言,把icon翻译为“迹”能够完美地体现出这一思想——阅读活动作为一个兴发着的“时间意识”或者“时间视域”就是或者就像一个“踪迹”“痕迹”“足迹”一样,因此,又可以把审美活动所呈显的“时间意识”称为“时间迹”或者“时流之迹”。
(二)“等不离于不即”——对纯文学进行强制阐释的机制
一旦构成纯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或者符号被改动,奠基于原初构成之上的特定时间意识便会发生“变化”,而且这一“变化”准确地说应该是“退化”或者“衰退”,这一“退化”与“衰退”不是半斤八两、可有可无的,而是“致命”的——“美”的变成了“丑”的,变成了“平庸”的,换言之,这是一种真正的“去势”!当然,在这里所说的“纯粹文学作品”正是指一个纯粹以审美愉悦为目的或价值的审美活动中的审美对象,而这一审美对象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自立、自足、独善其身的存在者,而是一个构成意向活动的相关项而已。只有在直接性的、原发性的审美活动中才如其所是地存在,才呈现出其审美价值。因此,钱钟书认为,如果把把准文学作品空间构成的不固定性、可更张性强行施之于纯文学作品,那就会完全破坏审美活动,他说:“如《说卦》谓乾为马,亦为木果,坤为牛,亦为布釜;言乾道者取象于木果,与取象于马,意莫二也,言坤道者取象于布釜,与取象于牛,旨无殊也。若移而施之于诗:取《车攻》之‘马鸣萧萧’,《无羊》之‘牛耳湿湿’,易之曰‘鸡鸣喔喔’,‘象耳扇扇’,则牵一发而动全身,着一子而改全局,通篇情景必随以变换,将别开面目,另成章什。毫厘之差,乖以千里,所谓不离者是矣。”⑩通过钱钟书所列举的例子可以看出,如果以内涵、含义相近或相同的语言、比喻来更换准文学作品的语言或者比喻,还不致使其意义受到影响或者伤筋动骨式的影响;而如果以内涵、含义相近的语言、拟象来更换、改变纯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与拟象,由美而丑,由美而庸,这是完全无法忍受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好的结局,那就是“别开生面,另成篇什”,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全新的创作与作品了,对于这一作品的阅读与欣赏当然也就是另外一个审美行为了。
当然,钱钟书的这一思想也有极大的遗憾与缺憾,主要体现在——对审美活动所呈显的原初时间视域构成还只是一个潜隐性的论述,尤其是没有把作品空间构成的这一精彩思想置入到审美活动或者文学欣赏活动这一前提下,更准确地说,是没有把审美活动作为一种有别于真、善、信的价值的寻求及呈现活动的原初状态作为前提,因此,钱钟书虽然已经在文中陈述了准文学的价值在于说理陈义,却没有直接说出纯文学的价值在于纯粹的美感或愉悦;虽然他透辟地、创造性地论证了准文学与纯文学在空间构成上的本质区别,却没有道出纯文学空间构成的“不离”特性实际上所指的是审美活动的流畅性,或者作为时间意识的流畅性。
在此,钱钟书给出了如何对待准文学的最佳方案,他不持过度的审美主义立场,他说:“哲人得意而欲忘之言、得言而欲忘之象,适供词人之寻章摘句、含英咀华,正若此矣。”(11)这意味着把那些以说理、求知、寻道为己任,同时在文辞上很动人、很形象、富有感染力或者尤其善用比喻、象征、寓言的文字,都通过由“不即”变成“不离”的方式,成为了文学作品。由此而言,很多思想家、哲学家、政论家、科学家、批评家们的著作便进入了文学史编纂者的视野,成为一种常态。
但是,这一把准文学视为文学的做法与动作却不能回返过来,把纯文学视为准文学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钱钟书说:“苟反其道,以《诗》之喻视同《易》之象,等不离者于不即,于是持‘诗无通诂’之论,作‘求女思贤’之笺;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丧所怀来,而亦无所得返。以深文周内为深识底蕴,索隐附会,穿凿罗织;匡鼎之说诗,几乎同管辂之射覆,絳帐之授经,甚且成乌台之勘案。自汉以还,有以此为专门名家者。”(12)“诗无通诂”或者“诗无达诂”之说始于汉代,与刘向、董仲舒有着密切关联,抑或也是当时流行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惯习、窠臼;其核心观念就在于背离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兴发着的、流畅的时间意识在空间构成上顽强的固定性——即钱钟书所言“不离”之根本特性,对构成文学作品的局部文字或者语言进行强制阐释,离开语言或由语言呈显出来的形象进行任意、随意阐释,这也就是本文在第一节所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典型的强制阐释案例之一就是“礼教”对于“诗”的僭越。
以“礼教”强制阐释“诗”,错的并不是“礼”自身,也不是“政治”“教化”“道德”自身,而是“强制”这一接受或阐释策略与机制。钱钟书在论及毛诗解《诗经·狡童》为“刺忽”之意时说:“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此可以考史,可以说教,然而非谈艺之当务也。其在考史、说教,则如由指而见月也,方且笑谈艺之拘执本文,如指测以为尽海也,而不自知类西谚嘲犬之逐影而亡骨也。”(13)这一强制阐释或许以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强词夺理来进行,比如常常衍化为一种文学教育、文学教材或者教法、文学水平考试的强制性的制度设计,上述钱钟书在著述中数十次讽刺的“求女思贤”就是一种表征强制阐释的文学制度;另外,强制阐释也通常以一种极为宽容、宽松、自由、大度的解释理论或者接受、鉴赏理论的面目示人,比如强调接受者的个体差异、文本的多层次解读潜力、解释者的兴趣或者思想的差异与变化等等。可见,强制阐释的权力根基、策略与托词是极强大的,这就更加凸显了钱钟书从审美活动作为时间意识的空间构成完整性角度,反对强制阐释、持守确当阐释思想的重大贡献。
从世界美学史及文艺理论史而言,钱钟书是第一位对审美价值与类审美价值、纯文学作品与准文学作品之间的差异进行系统比较的学者。自此而言,他称得上是一位世界级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
①②③⑤⑥⑦⑧⑨⑩(11)(12)(13)钱钟书:《管锥编》第1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23、23、24、24、25—26、23—24、23—24、24、27、27—28、218—219页。
④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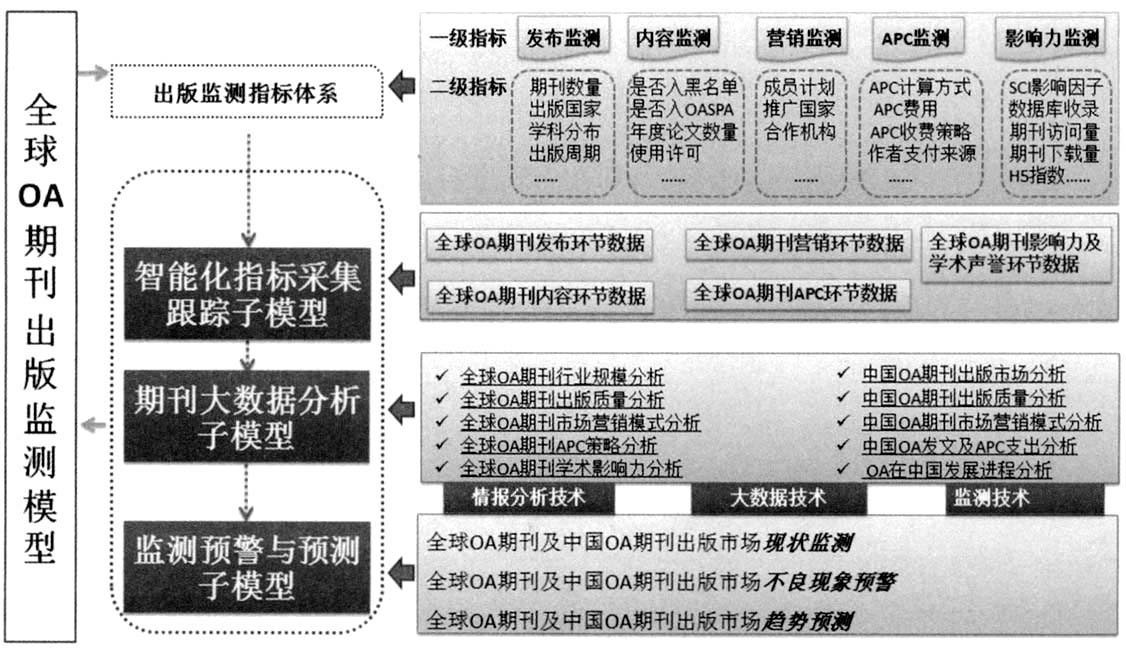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