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社会学最初曾十分关注剧烈现代社会变革及其导致的人生难题,同时努力开展应对人生难题的启蒙教育。但之后教育社会学却因追求“社会学化”,日益看重以社会理论剖析学校教育,以福柯、布尔迪厄等社会学大师的理论来研究学校教育由此变成当代教育社会学主流进路。依靠社会理论剖析学校教育,有助于教育社会学在学术上超越一般意义的教育学,但被社会理论束缚也会使教育社会学远离现代社会现实及人生难题,淡忘教育社会学当初为应对人生难题而生的启蒙教育努力。要想克服这些局限,教育社会学就须重建直面现代社会人生难题的学术视野及教育关怀。
关键词:教育社会学;社会理论;现代社会;人生难题
2016年11月,北京大学心理健康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文凯发表公开演讲,指出“北大四成新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30%北大学生竟然厌学,只因得了空心病”。之后,更有北大学子夏麦现身说法,坦言自己就曾遭遇“空心病”,并提请人们注意当下“呈上升趋势的虚无主义”[1]。徐文凯、夏麦等人的演讲及自述迅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时间“人生有何意义”之类的话题充斥众多论坛。人文社会学界也有不少学者积极参与探讨,其中有学者还提出,人文社会学科要想积极回应近些年愈演愈烈的人生问题,就必须调整当前的学术生产方式及课程内容。贺照田便强调,“如果人文研究对于一个具体生活着的人,对于他的身心状态改善收效甚微,那就有效性而言,此种研究仍不是‘够格’的人文研究”,“人文研究者应当重思自己的工作”[2]。人文社会学者的反思表明,新世纪以来的人文社会学科大体仍未突破上世纪90年代发现的学术生产局限,即远离经济社会转型期芸芸众生的现实人生及问题,以至于得等到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之类的残酷现实摆在眼前,人文社会学者才意识到,看似无比繁荣的学术生产其实往往很难与现实人生及问题搭上关系,进而也才会想到调整学术生产路向,努力贴近现实生活,以求能提供有益的人文知识或教育支援。教育社会学作为人文社会学术活动之一,也应在观照现实人生及问题的基础上,展开反思与变革。本文之所以提出“现代社会的人生难题”这一理论框架,即是为教育社会学直面现实人生问题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学术进路,以推动教育社会学的反思与重建,使教育社会学也能为社会教育贡献些许有益的学术理解及教育力量。
一、涂尔干与现代社会的人生难题
回顾教育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史可以发现,随着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教育与社会学》、《道德教育》等着作被陆续译成英文,涂尔干(E.Durkheim)开始被教育社会学界视为本学科的开山大师,其“对教育社会学的贡献”(诸如提出“教育是社会的产物,其功能在于促成年轻一代的社会化”等教育社会学理论)也随之成为教育社会学界难以绕开的经典论题[3]。但于本文而言,真正值得注意的还不是涂尔干在教育社会学领域有哪些开创性的理论贡献,而是涂尔干作为学院第一代教育社会学家,始终密切关注动荡现代社会转型,以及这一剧烈历史变迁进程导致的人生难题。他的社会学以及教育社会学都是为揭示、化解现代社会的人生难题而付出的学术实践和教育努力。言外之意,涂尔干并非后世过于专业化的教育社会学家,他不会将生产学界认可的教育社会学作为第一使命。对涂尔干而言,如何认识、应对动荡现代社会变迁及其造成的人生难题,才是其旨趣及重心所在。
如渠敬东注意到的那样,涂尔干所处时代“正值法国大革命后危机重重、疑影重重的时代”,其时“法国社会处于危难之中,极端个人主义盛行,怀疑情绪高涨,到处都是抽象的观念和成见;家庭纽带解体,经济竞争激烈而残酷,赤贫阶层大面积出现;在政治上,民众充满着暴戾之气,而上层政权因派系林立,合法性丧失经常瞬间性地倾覆和更迭,而紧接着全社会又再次掀起要求革命的浪潮”[4]。涂尔干即是围绕大革命前后的剧烈社会历史变迁进程展开其学术实践。由此不难看出,涂尔干的学术视野绝非像后世教育社会学那样局限于学校教育,而是关注全体现代人所生活于其中的动荡社会现实。即使作为教育社会学创始人,涂尔干必须关注学校教育,也是将学校教育置于动荡社会现实中加以考察,将学校教育视为“社会事实”(social fact)之一[5]213。而涂尔干之所以将动荡社会现实列为学术研究对象,正是为了认识剧烈现代社会转型导致的人生难题,同时寻求社会及人生重建的教育进路。起初在首部着作《社会分工》中,涂尔干曾将自身所见的动荡社会现实界定为“社会失范”:社会四分五裂,“所有权威都丧失殆尽”,到处都是“彼此斗争的各种势力”。至于社会的“失范状态”之所以会在“大革命”前后达到史无前例的严重程度,则是“近两百年来经济功能不断发展的结果”。“在过去,经济只能扮演次等角色,到今天则演变成最重要的事(prime importance)。很久以前,人们曾对经济嗤之以鼻,认为它属于下等阶层(lower classes),但现在我们却看到军事、宗教和管理等领域的功能都在围绕经济打转,只剩科学尚有些能力与经济对抗。虽然如此,科学也只是在某些实际事务上可以捍卫一点尊严。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在为与经济相关的职业效力”[6]xxxiii。经济一家独大,宗教、政府乃至科学等力量均听命于它,这正是现代社会转型或工业社会崛起的基本体制演变走势。现代社会转型进程中大多数人的人生难题乃至悲剧命运随之得以形成,“经济功能主宰了绝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成千上万的人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工业和商业环境里”。其中,“大多数人生都没有任何道德约束,……如此怎么可能养成利他主义、无私及牺牲等美德”[6]xxxiv。可以说,这就是现代社会转型给现代人带来的最大人生难题:除了忙碌赚钱外,很难有其他道德的意义;即使某一个体想要去追求更道德的人生,其道德理想也无以对抗扭转现代社会体制的经济至上原则。现代社会的经济至上趋势任其壮大下去,会有什么样的恐怖后果?除了在社会体制层面使国家、宗教、科学等发生功能畸变、社会失范外,最危险的结局就是现代社会的芸芸众生丧失传统的社会归属及人生意义,同时又不知道如何在现代社会转型进程中安顿自己,人生悲剧即因此随时可能发生。在第二部着作《自杀论》中,涂尔干提醒人们注意,无法在现代社会中安顿人生,极容易使人滋生“无政府主义”、“唯美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等“痛恨或厌恶现状”的思想,使社会弥漫“集体的忧郁”,从而导致“自杀率”上升[7]。
入职以来的现代社会观察使得涂尔干不得不思考如何应对现代社会的人生难题及悲剧命运。涂尔干曾提出要重建行业协会、法人团体等社会整合机制,还曾到原始社会寻找“宗教”力量。这些是学界熟知的涂尔干最主要的社会学实践。此外便是教育社会学界异常关注的教育社会学实践,诸如分析教育的代际文化传承作用,从社会秩序重建的角度建构由“爱社会”、“行为规范”、“纪律”等组成的“道德教育”[5]213-221。但本文更想从教育角度强调涂尔干的社会学及教育社会学实践,其实可以看成是为应对现代社会的人生难题而付出的启蒙教育努力。总之,涂尔干作为第一代教育社会学家,其所关注的第一问题乃是剧烈现代社会转型及其造成的人生难题,他的社会学及教育社会学实践除具有学术意义(揭示现代社会转型真相及人生难题症状),更是一次启蒙教育努力,试图向社会传播其社会危机发现及教育应对计划。虽然因为当时社会喜欢卢梭、伏尔泰等推崇个人自由的启蒙教育方案,并无多少人留意涂尔干的启蒙教育努力,但也不能因此否认涂尔干的宏伟学术视野与教育关怀,遗忘这位教育社会学创始人为应对现代社会人生难题付出的学术与教育努力。
二、转向以“社会理论”剖析学校教育
作为第一代教育社会学家的杰出代表,涂尔干也像其他典型的19世纪先锋理论家那样沉迷于“科学方法”[8],在其学术视野里,教育社会学也好,“科学”的社会学方法也好,都不足以取代“工业革命”引发的剧烈现代社会转型导致的人生难题,不过是他用于揭示、应对现代社会及人生危机的学术工具。进而言之,他是个“科学”的教育社会学家,同时更是康德或叔本华式的人文主义思想家,真切希望芸芸众生在道德失范的现代社会仍能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9],所以他不仅以“科学”的方法揭示现代社会及现代教育的激变现实,而且致力于以自己揭示的激变现实来教育(启蒙)国家、社会及芸芸众生,促使人们联合起来解决现代社会的道德失范与人生危机。涂尔干甚至还曾特意教育中小学教师,启发他们察古知今,避免被当时“流行的激情与偏见”牵着鼻子走,冷静思考日益混乱的社会与人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10]。然而涂尔干的学术及教育努力在19世纪晚期的学术界并没有赢得多少追随者,被“大革命”主导的政界更是没有谁会倾听于他。彼时真正影响大的乃是涂尔干所批判的种种“流行的激情与偏见”,尤其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为争取个人自由平等而提出的激进政治及社会变革理论。涂尔干认为,这些“流行的激情与偏见”只会加剧人类社会的分裂与冲突,进而使“经济功能”主宰一切,本已道德失范的现代社会更不可能重新变成和谐统一的道德共同体。只是无论涂尔干多么努力以自己的学术实践开拓不一样的启蒙教育,都无以扭转19世纪末日益激进的历史走势。直到1917年去世,涂尔干仍只能坐视个人主义的“激情与偏见”主导现代历史进程。具体到教育社会学领域,总体情况也是如此,涂尔干式的对于现代社会及人类整体命运的人文主义学术研究与教育关怀,逐渐让位于以现代社会某一特定人群的经验及利益诉求为基础而形成的自由平等理想,后者成为教育社会学内在的发展动力。
20世纪20年代,教育社会学尚未丢弃教育关怀,尽管其具体表现并非涂尔干式的依靠人文主义学术研究面向社会展开启蒙教育,而只是为“教师”及“学校教育实践”提供有用的“社会学知识”,毕竟也还有一定的教育努力,自“二战”结束以后,连这点有限的教育关怀及努力也不被看好了。美、英等国的教育社会学家组成的主流教育社会学皆热衷于用“Sociology of Education”替换“Educational Sociology”,“最活跃、最有成果的学者不再将自己视为教育学家,而是视为社会学家”。1963年,美国教育社会学会甚至转投美国社会学门下[11]。此即所谓教育社会学的“社会学化”,试图使教育社会学变成真正的社会学,并将这一点列为教育社会学发展的首要任务。教育社会学界因此不大愿意为学校教师及其教学实践提供支持,更不会像教育社会学开创者涂尔干那样,为应对现代社会的道德秩序失范与人生难题,以社会学及教育社会学等学术方式,面向整个社会发起康德式的人文主义启蒙教育,激励芸芸众生依靠理性力量,在四分五裂、意义迷乱的动荡现代历史进程中重新建立更为道德的社会秩序与人生意义。
转投社会学之后的教育社会学组织起了什么样的学术生产呢?以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教育社会学表现为例可以看出,最流行的学术进路乃是以伦敦政治经济学派的社会理论为基础对学校教育展开剖析。具体来说,即是把“社会流动”、“阶层不平等”等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揭示学校教育的阶层分化现象,尤其工人阶级学生学业成绩低下。到60年代又转向以伯恩斯坦代表社会语言学理论,进一步考察学校课程及教学语言如何不利于工人阶级学生取得优秀学业成绩。由此又引发70年代初的知识(课程)社会学转向,促成了以“知识与控制”理论为核心架构的“新教育社会学”的兴起。应该承认,教育社会学领域这些社会学化的学术重建有其正当的政治社会意义———因其旨在检视英国教育发展有没有兑现1944年定下的“教育为所有人”(education for all)的改革承诺[12],但从学术史角度看,仍不能忽视“社会学化”在为教育社会学确立新的学术范式及使命之余,也丢弃了教育社会学在涂尔干那里曾拥有的宏阔学术视野与教育关怀。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年代,当英美主流教育社会学转投社会学时曾译介涂尔干的着作,涂尔干随之得以进入英美主流教育社会学。但后者却把涂尔干视为“保守主义者”,无助于从社会流动、阶层分化、不平等的角度分析学校教育,为工人阶级争取学业成就平等[13],所以,即使终于发现涂尔干是教育社会学的开创者,也仍旧选择伯恩斯坦等人的社会理论。由此形成的教育社会学尽管同样关注现实,但如前所述,其理论视野已不再像涂尔干那样指向整个现代社会及人类命运,而是喜欢立足于现代社会某一特定人群(工人阶级)的经验及诉求架构理论。当然,工人阶级的教育及社会流动困境也是现代社会常见的一大人生难题,所以对于当代试图直面现代社会的人生难题的教育社会学者来说,上世纪50年代以来至70年代的教育社会学仍值得重视。转投社会学之后真正需要警惕的倾向是,一味屈从于社会理论,或把教育社会学仅仅理解为就是以各时期影响最大的社会理论来剖析学校教育,使教育社会学沦为社会理论的婢女,变成形式化的社会理论运用游戏,乃至无须考察任何人群的人生难题也可以生产教育社会学。
三、重建教育社会学的学术视野及教育关怀
以上只是从学术路径或理论建构层面分析教育社会学的后期演变。如果从学院体制来看,更能发现教育社会学由当初直面社会现实转向社会理论之后的潜在风险。简单说,当学院教育社会学的学术质量标准定为社会理论时,仅仅为争取学院体制上升或保住地位,教育社会学者便需将精力用于追随、消化学界最权威的社会理论。上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教育社会学界都发生过这类事情。当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福柯的知识权力等理论成为学术界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时,波尔、阿普尔、吉鲁等表现最活跃的新一代英美教育社会学者,都依靠精读这些权威社会理论得以在学院脱颖而出,成为新时期教育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但他们的着作揭示了多少人的现实人生困境呢?事实上,只要稍微浏览一下他们的主要着作便不难发现,其中往往就是以时髦的社会理论来批判政府学校教育改革政策及实施机制,连工人阶级学子的现实人生及难题都罕有涉及。当然,也不能否认上世纪50年代及70年代以来的社会理论转向,有利于教育社会学在学术上超越一般意义的教育学。后者给学术界留下的印象是“教学法”学,或中小学教师怎么上课,所以常遭学界歧视,被认为是“次等学科”[14]。50年代以来,教育社会学急于撇清与中小学教师及教学的关联,也与忌惮学界长期以来的差评有关,选择向社会学及社会理论靠拢,则确实为提高教育社会学的学术地位开拓了有效路径。甚至像布尔迪厄这样广为学界推崇的社会学大师也乐于投身教育社会学,并为教育社会学辩护。如布氏所言:“教育社会学是知识社会学和权力社会学的一个篇章,而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教育社会学远不是那种运用型的末流学科,它不像人们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门有益于教学人员的科学。”[15]布尔迪厄作为当代学术大师强调,以知识社会学、权力社会学等社会理论对学校教育展开研究,教育社会学便能成为学界重视的学术。难怪进入新世纪,教育社会学界仍乐于高举“用社会理论来研究教育”的学术大旗[16]。
近些年,教育社会学界甚至试图“进一步融入社会学阵营”[17],主流学术进路因此不会发生实质改变,依旧推崇以社会理论研究学校教育。只不过,社会理论来源于福柯、布尔迪厄、哈贝马斯等当代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几位大师,以至于让人觉得,教育社会学的首要使命就是“理解福柯、布尔迪厄、哈贝马斯”等几位大师的着作与理论[18]。不知道如果涂尔干看到当代教育社会学如此痴迷社会理论将作何感想?或许他又会像当年批判卢梭等人的激情言论一样,对当代教育社会学推崇的“再生产”、“知识权力”等流行权威社会理论展开批判,认为任由这些理论蔓延下去,只会加剧现代社会的分裂与冲突。由此会再度唿吁转向真正重要的全体人类都在遭遇的现实议题,即整个现代社会的道德失范及人类的人生意义危机。然而涂尔干终究早已作古。与此同时,教育社会学界也没有谁能在学术影响力上取代福柯、布尔迪厄等人。迈克尔·扬近些年倒是在调整学术视野,但他试图转向的却不是现代社会现实及芸芸众生的人生难题,仍是在知识社会学理论中展开探索。只不过由当初立足于工人阶级立场批判学校知识,变成了为各学科普遍认可的所谓“客观知识”叫好,论证这类知识是全体人类必须接受的“强力知识”(powerful Knowledge)[19]。
迈克尔·扬调整学术视野时曾向涂尔干学习[20],也从中得到理论启示:诸如从社会阶层入手研究学校课程,只会加剧教育领域的权力斗争,更重要的问题乃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和平统一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与课程。由此也可以进一步看出,当代教育社会学因长期被知识社会学理论束缚,往往只能在知识社会学理论之内调整议题,无法像涂尔干那样直面现代社会现实及人生难题。进而言之,面对本文开头提到的人生难题:在当下被经济力量主导的历史变革及社会转型进程中,包括“四成北大新生”在内的芸芸众生仍然在遭遇不同程度的人生意义危机,教育社会学要想作出学术回应,就须反思甚至跳出长期以来视之为“不二法门”的以社会理论剖析学校教育的学术进路,使学术视野及研究对象重新关注现代社会转型及其导致的人生难题。不仅如此,当代教育社会学还需重建涂尔干曾经有过的人文教育关怀,而不是只关注学校教育及其知识课程体系,且仅将它们视为社会理论的剖析对象。教育社会学者大可像涂尔干那样,通过学校或其他公共机制,面向整个社会开展人文启蒙教育,在动荡社会转型进程中重建道德秩序与人生意义。如此,教育社会学才可能为当代社会及人生切实贡献有益学术及教育力量。
参考文献
[1]夏麦.我所经历的“空心病”,一个名校90后的自白[OB/EL].2016-11-27.http://learning.sohu.com/20161127/n474242535.shtml.
[2]王逸凡,梁苑茵,整理.青年人普遍感觉人生无意义?中国当代的精神史危机[OB/EL].2016-12-16.http://www.thepaper.cn/news Detail_forward_1580183.
[3]Barnes,G.M.Emile Durkheim's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in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hought,Vol.11,No.3,1977:213-233.
[4]渠敬东.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涂尔干对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新构建[J].社会学研究,2014(4):112.
[5]Ottway,A.The Educational Sociology of Emile Durkheim,i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6,No.3,1955.
[6]Durkheim,E.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84.
[7]涂尔干.自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05.
[8]Victor,B.Durkheim,A Brief Memoir,in Sociological Review,Vol.10,No.2,1918:81.
[9]Lyons,M.Kantianism and Emile Durkheim's Ethical Theory.Honors Projects,1991.Schmaus,W.Rethinking Durkheim and His Tra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10]Derkheim,E.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Thought.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 Ltd,1969:13.
[11]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30-31.
[12]Banks,O.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1952-1982,i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Vol.30,No.1,1982:18-31.
[13]Davis,B.Durkheim and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n Britain,i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Vol.15,No.1,1994:3-25.
[14]Lagemann,E.C.An elusive science:The troubling history of education research.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15]朱国华.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图绘布尔迪厄教育社会学[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73.
[16]Dressman,M.Using Social Theory in Educational Research.London:Taylor&Francis,2008.
[17]Binder,A.J.Sociology of Education's Cultural,Organizational,and Societal Turn,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Vol.86,No.4,2013:282-283.
[18]Murphy,M.ed.Social Theory and Education Research:Understanding Foucault,Habermas,Bourdieu and Derrida.London:Routledge,2013.
[19]Beck,J.Powerful knowledge,Esoteric Knowledge,Curriculum Knowledge,in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Vol.43,No.2,2013:177-193.
[20]Young,M.et al.Curriculum and the Specialisation of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2015.
周勇.教育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的人生难题[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3):45-50.
更多教育论文,请关注一起问道论文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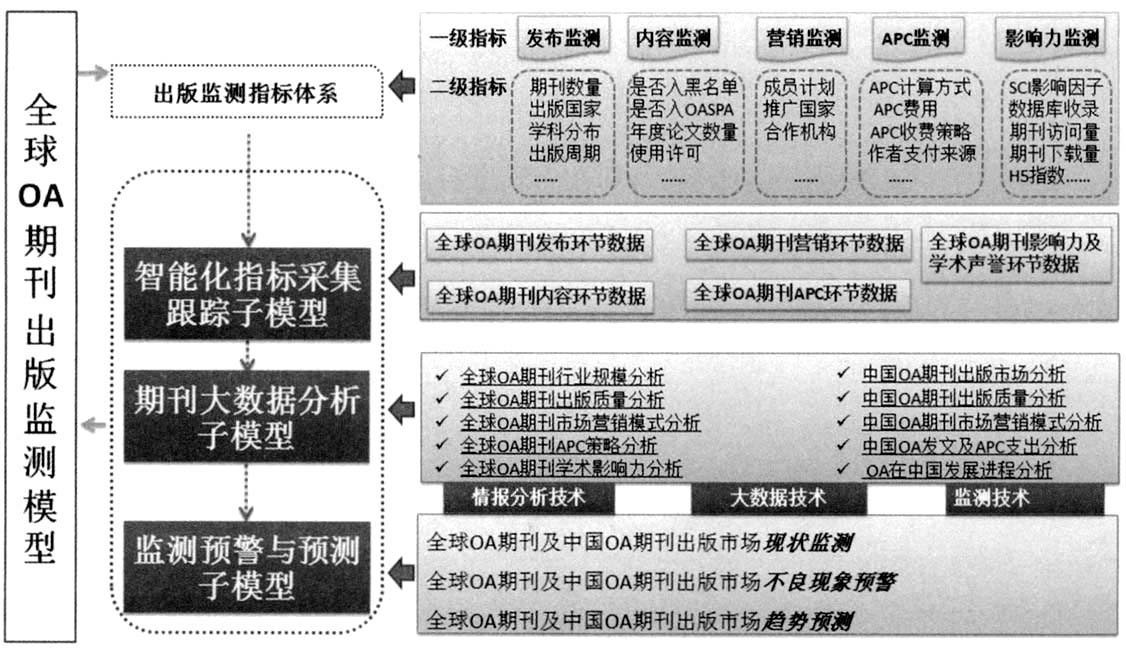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