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文学制度,它是有效保障本国的文学运动按照自身规定的轨迹运行的基础,因此,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互动的循环关系。当然,它可以是良性的,也可以是恶性的,这就要看这个制度对文学的制约是否有利于其发展,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定文学制度者是如何操纵和驾驭这一庞大机器的。

ISBN:9787521209143
作者:丁帆
2020年12月
《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以清末鸦片战争以后现代文学制度的萌芽期为研究起始点,下限到21世纪,在依托大量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纵向的史的体系和横向的空间比较体系,重点关注“有形文学制度”和“无形文学制度”如何建构、如何支撑和支配着文学史的发展走向等问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进行理论的审察和历史的分析,在宏观的理论和微观的历史细节之间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的变迁,具有突破性和创新性。
文学现象中的制度因素如何产生作用及影响于文学的实质性演变?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也是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制度研究的侧重点。作者们并非直接进行广义的社会学、政治学范畴中的制度研究,而是尤其注重对制度实践的考察,即文学遭遇和面对的制度性操作问题,而非一般理论或宏观意义上的制度问题。这一研究思路及观点对于当代文学制度建设及文化强国的战略都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使本书具有较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丁帆,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评委。发表文章400多篇,共500万字,出版主编各类著作40余种。培养博士、硕士生共160多人。
文学与制度的纠缠,以及制度对文学的干预与渗透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而复杂得多。从制度的角度研究文学是一个相对新颖的学术领域,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都为数不多。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学制度,作家的创作、文学文本、读者的阅读与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发生着紧密联系,作家的职业性和社团归属,作品传播对报刊和出版以及文学批评、文学论争、文学审查和文学奖励的参与等,共同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强大的制度力量。文学制度是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表征形式,厘清中国现当代文学百年发展过程中这些纷繁复杂、犬牙交错的文学制度,是一个繁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
本书把制度引入文学研究,将其作为一个重要视域,着重从文学制度与文学、文学制度与文学史写作、文学制度与文学理论的建构、文学制度与具体的文学现象等方面对我国现当代文学进行系统的研究,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空间,形成了新的文学研究格局,客观上也把文学社会学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
——孟繁华
文学制度研究可以称之为文学的过程研究和文学的生态研究。将文学制度和文学理论建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联系起来,文学的体制问题无论是对中国文论建设,还是中国文学史研究都该成为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学术话题。目前对文学的社会背景、文学的出版与传播、文学的社团与流派、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已经涉及了文学的制度问题,却鲜有专门论著上升到文学制度的理论高度,且缺乏制度研究的“自觉意识”。
《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一书,研究对象的时间上限划定在清末鸦片战争以后现代文学制度的萌芽期,下至21世纪,以文学制度研究为方法和切入角度,全方位梳理、分析和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系统论述了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建制化历史,不仅有利于阐明百年新文学历程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更可以为今后文学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有助于相关学术研究的推进和我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具有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陈晓明
绪言
毋庸置疑,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文学制度,它是有效保障本国的文学运动按照自身规定的轨迹运行的基础,因此,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互动的循环关系。当然,它可以是良性的,也可以是恶性的,这就要看这个制度对文学的制约是否有利于其发展,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定文学制度者是如何操纵和驾驭这一庞大机器的。
美国批评家杰弗里·J.威廉斯在《文学制度》一书的“引言”中说:“从各种意义上说,制度产生了我们所称的文学,或更恰当地说,文学问题与我们的制度实践和制度定位是密不可分的。‘制度’(institution)一词内涵丰富,而且往往带有贬义。它与‘官僚主义’(bureaucracy)、‘规训’(disciplines)和‘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同属一类词语。它指代的是当代大众社会与文化的规章与管理结构,和‘自由’‘个性’或‘独立’等词语正好处于相反的方向。从一个极端来说,它意味着文学的禁锢……更普遍的说法是,它设定了一些看似难以调和的国家或公务员官僚机构……我们置身其中,我们的所作所为受其管制。”毫无疑问,这种管制是国家政权的需要,也是一种对文学意识形态的管控,我们将其称为“有形的文学制度”,它是由国家的许多法规条例构成的,经由某一官方机构制定和修改成各种各样的规章与条例,用以规范文学的范畴,以及处理发生的各种文学事件,使文学按照预设的运行轨道前进。在一定程度上,它有着某种强制性的效应。
还有一种是“无形的文学制度”,正如杰弗里·J.威廉斯所言:“‘制度’还有一层更为模糊、抽象的含义,指的是一种惯例或传统。根据《牛津现代英语用法词典》所载,下午茶在英国文化中属于一种制度。婚姻、板球、伊顿公学亦然。而在美国文化中,我们可以说棒球是一种制度,哈佛也是一种制度,它比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校园具有更深刻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说,一种文化形态就是一只无形之手,它所规范的“文学制度”虽然是隐形的,但是其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构成文化形态的约定俗成的潜在元素也是一种更强大的“文学制度”构成要件,我们之所以将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称为“无形的文学制度”,就是因为各个时代都有其自身不同的文化形态特点,大到文化思潮,小至各种时尚,都是影响“无形的文学制度”的重要因素。
我们的百年文学制度史,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两岸文学制度史往往是以文学运动、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乃至会议交流等形态呈现出来的,它们既与那些“无形的文学制度”有着血缘上的关联性,又与国家制定的出版、言论和组织等规章制度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它们之间有时是同步合拍的互动关系,有时却是呈逆向运动的关系,梳理二者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历史关系,便是我们撰写这个制度史的初衷。因此,我们更加重视的是整理出百年来有关文学制度的史料。
基于这样一种看法,我们以为,在中国近百年的文学制度的建构和变迁史中,“有形的文学制度”和“无形的文学制度”在不同的时空当中所呈现出的形态是各不相同的,对其进行必要的厘清,是百年文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任务。从时间的维度来看,百年文学制度史随着党派与政权的更迭而变迁,1949年前后的文学制度史既有十分相同的“有形”和“无形”的形态特征,也有不同之处。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地域特征(不仅仅是两岸)主要是受那些“无形的文学制度”钳制,那些可以用发生学方法来考察的文学现象,却往往会改变“有形的文学制度”的走向。要厘清这些纷繁复杂、犬牙交错的文学制度变迁的过程,除了阅读大量的史料外,更重要的就是必须建构一个纵向的史的体系和横向的空间比较体系,但是,将这样的体系结构统摄起来的难度是较大的。
在决定做这样一项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抱定了一种客观中性的历史主义的治学态度,也无须用“春秋笔法”进行阐释,只描述历史现象,不做过多评判。后来发现,这也是国外一些文学制度史治学者共同使用的一种方法:“我们必须采取更加直接的方式以一致立场来审视文学研究的制度影响力,不要将其视为短暂性的外来干扰,而要承认它对我们的工作具有本质性影响。与此相关,我们需要不偏不倚地看待人们对制度的控诉;制度并不是由任性的妖魔所创造出来的邪恶牢笼,而是人们的现代组织方式。毋庸置疑,我们当前的制度所传播开来的实践与该词的贬义用法相吻合,本书的许多章节都指出了制度的弊端,目的在于以更好的方式来重塑制度。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精明地建议,我们必须‘在断言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一词时抛开惯有的刻薄讽刺,要区别对待具体的制度选择,而不是一股脑地对其谴责(或颂扬)’。”其实,我们也深知这种治史的方法很容易陷入一种观念的二律背反之中,当你在选择陈述一段史实时,选择A而忽略了B,你就将自己的观念渗透到了你的描述中了。所以,我们必须采取的策略是,尽力呈现双方不同的观念史料,让读者自行判断是非,让历史做出回答。
按照《文学制度》第一章撰写者文森特·B.里奇《构建理论框架:史学的解体》的说法:“建构当代理论史有五种方式。关注的焦点既可以是领军人物,或重要文本,或重大问题,也可以是重要的流派和运动,或其他杂类问题。”
毫无疑问,构成文学制度的前提要件肯定是重要文本,没有文本当然也就不会产生与之相对应的许许多多围绕着文学制度而互动的其他要件。就此而言,我们依顺历史发展的脉络来梳理每一个时段的文学制度史的时候,都会凭借每个历史时期文学制度的不同侧重点来勾勒它形成的重要元素。虽然它们在时段的划分上与文学史的脉络有很多的交合重叠,但是,我们论述的重心却落脚在“有形文学制度”和“无形文学制度”是怎样建构起来并支撑和支配着文学史的发展走向的。
中国自封建体制渐入现代性进程以来,无疑是走了一条十分坎坷的路径。我们认为,不管哪个历史时段发生的制度变化,都是有其内在因素的,于是,我们试图从其变化的内在肌理来切分时段,从而描述出它们发展的脉络。
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世界格局带来了中国的大变局,与之相应的中国文学制度便开始有了现代性的元素。清末拉开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序幕,文学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当然,就现代文学制度而言,这一时期还只是新的文学制度的萌芽期。现代文学制度之所以于此时浮出水面,一方面得益于文学观念的转型,另一方面,更在于相关结构性要素渐趋成熟并建构起一个相对完善的文学、文化运作系统。
无疑,北洋政府对建立文学制度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的,而真正将其现代性的元素进行放大,甚至夸张的,还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文学革命”最终完成了文学观念的转型,与此相应,文学制度的相关结构性要素也在民国成立之后得到了飞速发展,并形成了一个较前更趋复杂严密的体系。当然,民国的文学制度及至后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可否认的。
抗战时期,中国版图上存在着多股政治势力,国土分裂成了多个碎片化的地理政治空间。以广义的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而论,每一政治空间的政治势力都在追求各自的文化领导权,都在推行各自的文化与文学政策。在这种众声喧哗的情势下,文学制度的有效性是发生在不同的时空之中的,当然,最有影响的还是延安的文艺政策,它深刻地影响着以后几十年文学制度的建构。
在共和国的文学制度史中,之所以将“十七年”作为一个时段,就是因为这个时段的文学制度的建立对以后几十年的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有特点的是,从此开始,文艺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文学机构的创建与改革,文学领导层的人事安排,几乎都是通过会议来实施的。在历次文代会和作代会之中,第一次文代会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的基本框架。解放区文艺被确立为文学的正统,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宣告成立,来自解放区、国统区的作家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各安其位,创办了全国文联、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文艺报》《人民文学》。在此基础上,各大区、各省市纷纷召开区域性的文代会,成立区域性的文学机构,创办地方性的文学刊物。第一次文代会是当代文学制度建设的奠基石。
文学制度发展演变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种极其奇特的现象,即:一方面,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旧文学制度而言,“十七年”的文学制度在各个层面上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制度之变与体制之新已经令很多作家深感“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相对于意识形态的要求而言,“十七年”文学制度则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成为不得不革除的陈旧落后的体系。这种“新”与“旧”的巨大错位和反差,充分反映了文学制度史的时代复杂性及其独特规律。在这种强烈的“制度焦虑”的驱使下,“十七年”文学制度成为“旧制度”从衰落到崩溃,“新制度”建设则紧锣密鼓、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
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中国“十七年”间确立和完善的文学制度也被摧毁。几乎所有的文学建制都失去了应有的功能,文学的机构(包括出版传播、文学生产、文学评奖等)都因为高度的集权而趋于凝滞。因此,随着“文革”的结束,文学制度面临着恢复和重建的迫切任务。在此重建过程中,文学的新的方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得以最终确立。恢复和重建之后的文学制度,成为使党和国家文艺政策得以贯彻执行的重要保障机制。随着文艺政策的摇摆与起伏,文学制度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无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制度恢复、波动、起伏最活跃的年代,而1984~1985年之交召开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是文学组织和体制的又一次调整,这一组织化、体系化的调整对此后一段时间里的文学创作、批评,乃至文学制度都产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影响。
重建文学制度,首先亟须恢复和重建的是文学机构——文联与作协。文联和作协最高层面的机构组织是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各省市地区都恢复和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建制,全国一体化的、具有隶属关系的各级文联与作协成为文学制度有力的执行机构。这两个层级化的组织机构是整个文学制度的核心。有了这个机构,所有的体制内的作家就会以不同的级别而成为每一层级的文学干部,从而处于文学制度这一庞大机器中齿轮与螺丝钉的地位,使文学创作的动员与组织就成为一种常态性的运作。
当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对“文革”及“十七年”期间的回顾、总结、反思的不断深入,文学创作中开始突破原来既定的政治方向和范围,偶尔出现挑战禁忌或者溢出体制边界的某些倾向。一方面,文学媒体为这些作品提供了发表的平台;另一方面,媒体也成为党进行文学性质的宣传、方向的引导、批评的展开的重要阵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个意味深长的年代。它尚未远去,但已经成为当代思想文化讨论中一个难以绕开的源点,许多问题可以溯源于此。无疑,消费文化的大潮席卷而来,这对中国的文学制度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中国日益深入世界市场的竞争之中,知识生产和学术活动已经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部分。“人文精神大讨论”骤然兴起表明了人文知识分子共同感觉到了问题的压迫性,而它无法导向某种具体价值重建的结局,也拉开了一个认同困惑的时代帷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超出了他们所熟悉的历史和知识范畴,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与文化的思潮,凸显出了让人措手不及的尖锐矛盾。文学在这次文化变异的激烈冲突与重组中被抛到了边缘,文学制度也在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兴起催发了文学制度的重构,自由写作者的出现和网络文学的出现,也给文学制度的重构带来了新的难题和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制度是呈悄然渐变状态的。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中国大陆基本的格局是继续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加强、完善和延伸,尽管出现了新的现象和特征,但并未出现一条明显的文化分界线。在二十世纪末,公众文化领域和国家政策层面都涌动着一种“世纪末”的总结趋势,但就具体文化发展来看,一种文化裂变的嘉年华并未出现,各项政策法规和文化制度跟随经济变革平稳推进,文学生态环境未发生明显变更。但文学制度有了新的发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制度的基础上,呈现出深化和复杂化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机制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随着文学网站和文学社区的构建,网络文学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网络文学产业化的运行、监管制度的建立,对网络文学的稳健发展都具有必要性。随着影视业的发展,影视制作与作家之间形成了新的关系,影视改编将文学接受置入一种新的格局之中,对当代文学生态产生着重要影响。民间刊物已经成为当代诗歌得以流传的重要形式,民刊官刊化、民刊弥补体制内文学制度的不足,都成为值得关注的话题。在当前的文学评奖中,官方奖项的评选和颁发过程亟待调整,民间奖项需要通过文学观念的调整获得更大的公信力。从文学激励角度来看,调整后的两者都将大大有助于文学创作质量和积极性的提高。
毋庸置疑,台港百年来的文学制度史与大陆文学制度史既有重叠之处,更有相异之处。二十世纪台湾文学制度受着殖民化和“民国化”延展的影响,到1987年解严之后,又发生了质的变化。而香港的文学制度却是在历经殖民化的过程中,在1997年才悄悄发生了变化。
在文学制度的研究当中,对于文学社会化过程的考察是必要的。由此,在不同的时空场域下来考察不同地域文学活动背后的无形之手——文学制度的运作,也必须贴近、还原适时的文学活动具体情况。日据时期台湾的文学制度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尽管在大的新文学传统范围里面,台湾文学传统与大陆文学传统相互呼应,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孤悬”、文化受容的“多元”,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在发展样貌上有着自己的地域特性。“文学制度”的概念引入,以及对文学制度在形成、发展全过程中诸方面特色的描述,乃至对文学制度诸多组成要素,如文学教育、文学社团、出版传媒等方面的勾勒,可以给予读者一个相较以往文学史之单线描述而言更加复杂、参差的立体文学生态景观,使其得以窥见在文学史复杂表象背后更具棱角,并影响着文学制度建构之另一面。
综上所述,我们在撰写这部制度史的过程中,尽力试图将文学史的发生与制度史的建构之间的关系勾连起来分析:外部结构是法律、规章、出版、会议、文件等大量的制度“软件系统”;内部结构则是文学思潮、现象、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等“硬件系统”。只有在两者互动分析模式下,才能看清楚整个制度史发展走向的内在驱力。虽然付出了努力,但囿于种种原因,比如尚不能看到更多解密的文件资料,这会影响我们对某一个时段的文学制度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尽管有遗珠之憾,但我们努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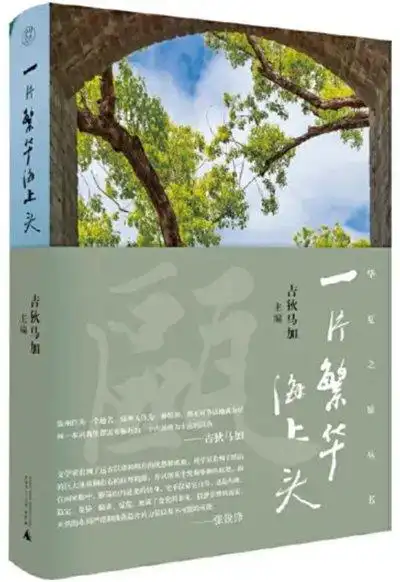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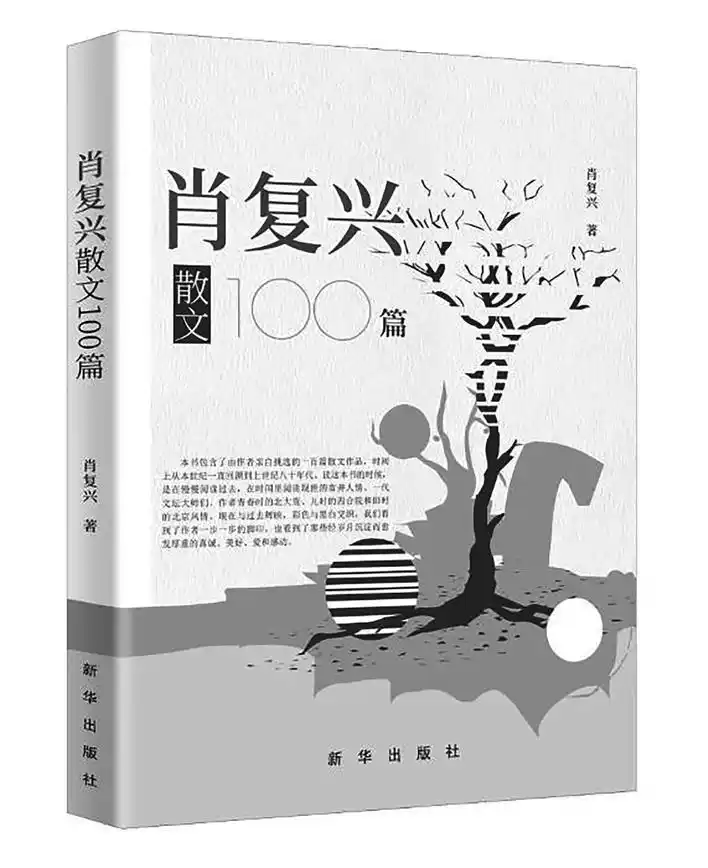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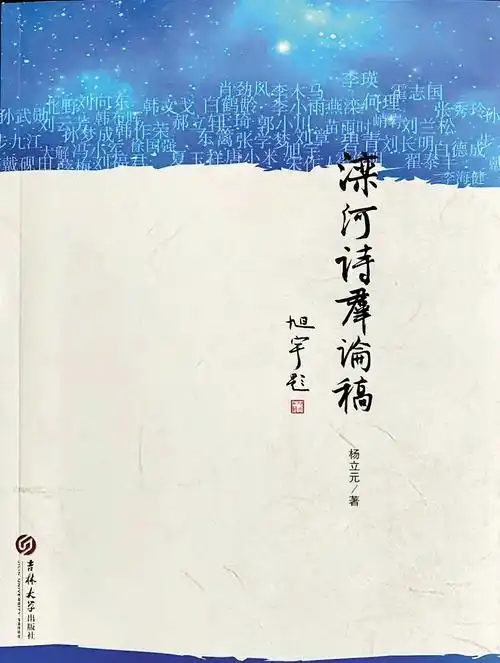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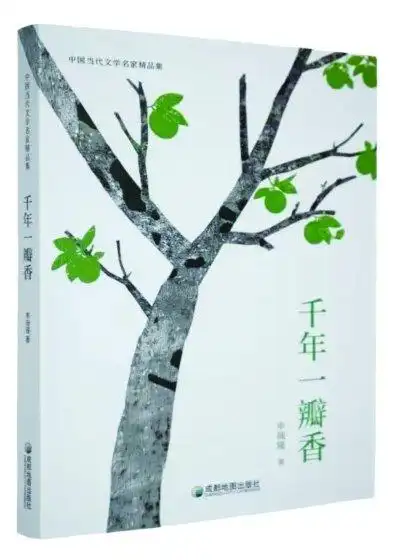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