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我国留守儿童生存现状堪忧。我们不仅要在理念上更新儿童观及儿童权利观,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落实于儿童权益保护的立法和实践领域,完善留守儿童的监护制度,更应对留守儿童的生存权保护具体落实到实施细节上,将留守儿童生存权保护视为一个动态过程,从事前的预防、事中的监督、事后的救济三个层次上予以全方位的保护。
关键词:留守儿童;生存权;法律保护
2015年6月9日晚,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四名留守儿童服敌敌畏中毒死亡。四名留守儿童系同一家庭的四兄妹,老大十三岁,最小的才五岁。事件发生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十分关切并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对各地加强督促,把工作做实、做细,强调临时救助制度不能流于形式,对不作为、假落实的要严厉整改问责,悲剧不能一再发生。据警方披露,自杀前,十三岁的哥哥留下遗书称:“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十五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为什么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孩子会对生活如此绝望、对生命如此冷淡?
据新华网记者实地走访调查发现,四名儿童生前相依为命,并无其他人照顾,母亲离家出走多年,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离家出走后,父亲也只是在外出打工的一年后寄来七百元生活费,平常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四个孩子的全部生活来源就是父亲和老大每月的低保费,他们死前的最后一顿晚餐是玉米和酸菜。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四名儿童的“生存”根本没有得到最起码的保障。虽然生命是他们自己选择放弃的,但他们只是几个理性和意志远未发育成熟的儿童,这场悲剧的发生难道仅仅只是这几个儿童自己的过错吗?他们的生存权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吗?这起悲剧决不仅仅只是特殊的、没有代表性的个案那么简单,它折射出我国目前留守儿童群体生存权保护机制的滞后。
一、我国留守儿童生存现状及其生存权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已连续超过半年以上而被留在家里,需要其他亲人照顾的未满16周岁的儿童。依据地区的分布,可分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城镇留守儿童。根据留守儿童留守方式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以下四类:(一)自我留守型,父母双方均外出,单独留守的儿童;(二)“单亲”留守型,父母一方外出,与另一方一起留守的儿童;(三)隔代监护型,父母双方均外出,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儿童;(四)上代寄养型,父母双方均外出,与父母同辈的亲戚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其中(一)类是真正意义上的“留”、“守”儿童。其他三类的生活侧重点在“留”而“守”的意义并不大。2013年5月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根据《中国2010年第6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我国仅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就高达6102.55万,占全国儿童总人数的21.88%,且总体规模还在进一步扩大中。如此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其生存状况是我们必须要予以高度关注的。
那么,目前我国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怎样呢?应该说,从整体上来看是不容乐观、令人担忧的。大部分留守儿童生活上得不到应有的照料,不少儿童自己洗衣、做饭、砍柴、喂猪,甚至还要照顾弟妹、干农活,生活的重负全压在了他们稚嫩的肩膀上。由于糟糕的生活条件,留守儿童的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有些儿童厌学甚至弃学;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也是十分令人担忧的,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得很多儿童身体发育迟缓;不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也存在不小的问题,表现为焦虑、孤僻、冷漠、沮丧、抑郁等。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一些不法分子往往趁机拐卖留守儿童或性侵留守女童,还有一些留守儿童不幸发生溺水、触电、高空跌落等意外伤亡事件。面对留守儿童如此生存现状,我们不禁要问,其生存权保障何在?
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首次提出儿童生存权,公约第六条明确规定缔约国应确保儿童固有的生命权,并尽最大可能保障儿童的存活与发展。我国2006年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儿童生存权是一项需要给予特殊、优先保护的权利。日本学者大须贺明认为,生存权是指健康且带有一定文化内涵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权利,最低限度生活是指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能过像人那样的生活。我国学者郝卫江认为,生存不仅指一个人生而固有生命,还包括在恶劣环境的威胁下获得生存;不仅包括衣食温饱,还包括个人的快乐,个人与他人及周围环境的和谐共生;不仅指生命的延续,还要有尊严地活着。据此,笔者认为,儿童生存权应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儿童生存应具备的生命安全和生活保障的基本权利,具体包括生命权、健康权、温饱权等;二是儿童拥有快乐和享有尊严的较高层次的基本权利,包括身份权,受照顾权,受抚养权,不被虐待、剥削和遗弃的权利,安全的社会环境权等。
以此观照,目前我国留守儿童的生存权并没有得到真正实现,如何保障留守儿童生存权的实现已成燃眉之急。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不仅影响到留守儿童个体的成长,还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因此,如何在法律制度上构建一个完善有效的留守儿童生存权保障体系,是笔者认为亟待反思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我国留守儿童生存权法律保护不足的原因
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一部专门保护留守儿童权益的法律,留守儿童的法律保护只能参照一般儿童保护的法律。对于儿童生存权的法律保护,我国实行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以其他保护儿童出生与健康、医疗与卫生、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为辅的保护体系。虽然我国关于儿童生存权保障的法律法规不少,但是对于保障留守儿童的生存权却是鞭长莫及。《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对儿童生存权提出保护的要求,但是在具体保护措施的实施上并没有作出规定。其他法律法规虽然在预防儿童出生缺陷、提高儿童健康质量、保障儿童食品安全和乘坐校车安全等方面起到了保障作用,但是对于解决留守儿童生活、健康、安全等问题却是杯水车薪,也没有起到“对症下药”的作用。可以说,对留守儿童的生存权的法律保护是缺失的。
留守儿童生存权的利益诉求,是在生活上当父母抚养或监护缺位时可以得到相应的照顾和妥善地安置,在健康上能享有最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和医疗保障措施,在安全上可以得到有效的引导和保护,在学习上可以享有充足的时间并得到学校和老师的帮助指导,在亲子关系上可以享有与父母团聚的机会和时间,享有童年的快乐和尊严。然而,在我国现有的儿童保护法律机制下,留守儿童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是无法得到满足。
我国留守儿童生存权法律保护缺失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我国传统儿童观落后,阻碍了儿童法律保护体系的建构和完善。
我国传统儿童观是建立在“父权”统治观念下的,儿童一般被看作家庭的附属品或牺牲品。即使在儿童被称为“小皇帝”的今天,人们对儿童的认识仍未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没有将儿童作为独立于成人的主体予以对待。传统儿童观导致了目前我国儿童权利观的落后,虽然我国法律承认儿童是权利的主体,但是儿童作为权利主体的能动性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儿童的权利实现只能依赖于成人。相应的,儿童法律保护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也受到一定的阻碍。
(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我国儿童法律保护的理念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儿童最大利益是指,儿童是拥有权利的个体,是基本人权的享有者;儿童利益优先,当存在不同利益时对儿童最大利益应做首要考虑;当一个决定涉及儿童利益时,在决策中必须评估对儿童造成的影响,而且决定的理由和标准必须证明儿童最大权利已被明确考虑。
留守儿童的大规模出现是儿童利益与家庭利益、社会利益发生矛盾的产物。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一方面因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也需要改变家庭生活状况,谋求更好的发展,因此大量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这就使得留守儿童的大规模出现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状。儿童同样需要生存和发展,父母的离开破坏了家庭功能的完整性和儿童个体发展的有益性。在利益平衡时,我们并没有坚持“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而是将儿童利益置于家庭利益、社会利益之后。在制定社会发展的宏观政策时,我们也没有充分考虑留守儿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以致我国对留守儿童权益的法律保护严重滞后甚至缺位。
(三)对于儿童的监护,过分依赖“亲属监护”。
我国目前对儿童的监护,是实行以“亲属监护”为主、组织监护为辅的监护制度。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打工,虽会将子女委托于其他亲属监护,但是并没有从心理上重视自己对子女的实质责任和义务,往往导致重养轻教而忽视留守儿童个体的生存发展。这与我国的“亲权”与监护不分也是有关的。“亲权”是家庭关系中父母与子女之间最基本最核心的关系,即父母基于身份,对未成年子女以教养保护为目的的权利义务集合,“亲权”既是父母对子女享有的权利,也是父母对子女应履行的义务。而在我国由于“亲权”理念的缺失和监护制度的不完善,所以在儿童保护立法上没有重视父母对子女教养的权利和义务。当留守儿童的生存权遭受侵害或是保障不力时,我国法律保护是缺位或是不济的。
三、完善我国留守儿童生存权法律保护的建议
要解决留守儿童生存保障问题,关键在于从法律制度和程序上予以保障。
首先,我们应树立科学的儿童观及儿童权利观。儿童是社会、家庭的组成者,是独立的主体,儿童与成人一样都是社会实践的参与者。儿童是权利的拥有者,生存权于儿童而言本身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儿童应该和成人一样享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因为其个体的特殊性,对于儿童权利我们更应予以特别的保护。在儿童权益的立法指导思想上,应树立新型的儿童观及儿童权利观,将儿童置于与成人同等的道德地位予以关注和保护,保障儿童在其权利实现过程中享有主体地位。
其次,“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应是儿童权益保护的首要原则。虽然我国承认《儿童权利公约》强调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但是在保护儿童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作为指导性原则予以确立。因此,在儿童权利的实现过程中,“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也没有起到补充儿童法律保护的空白和不足的作用。在留守儿童生存权保护的法律建构和完善中,应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作为留守儿童保护的首要原则。这样才能弥补儿童权利保护法对留守儿童保护的缺位,突破其局限性,也才能在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的立法与实践中真正做到尊重儿童利益和需求。
最后,应不断完善留守儿童监护制度。对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的监护,应实行委托监护,在制度上和程序上予以有效监督,并适时引入国家监护制度,保障留守儿童生存权的实现。
当然,这些都只是从宏观的角度对儿童生存权的法律保护提出建议。具体到留守儿童生存权的保护措施,则应遵从李克强总理一再强调的“把工作做实、做细”原则。留守儿童生存权的法律保护不应仅停留于法律条款的规定,而应落实到具体的法律实施上。对留守儿童生存权的法律保护,我们应将其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从事前的预防、事中的监督、事后的救济三个层次上,对留守儿童生存权予以全方位的动态保护。
(一)留守儿童生存权法律保护的事前预防措施
留守儿童的生存权应是一般生存权的组成部分,具备和一般生存权同样的法律性质,属于社会权的一种,国家对其具有保护和干预的积极义务。由于儿童自身的脆弱性,儿童不可能像成人一样成为自己生存的自助者和自救者,这就需要在儿童权利遭受侵害前,国家对儿童生存权的保护进行事前的积极干预,以确保儿童生存权能最大限度的实现。
针对留守儿童生存权的法律保护的事前预防,国家立法应制定强制性规定,父母外出打工前有义务将儿童委托于第三人(应不限于亲属之间,可将监护权委托于儿童保护组织或机构)监护,并向基层组织报告委托监护的情况,接受委托的第三人应恪尽妥善监护义务,否则应承担监护失职的责任。基层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和居委会,有对外出打工方和接受委托方负有监督义务,确保留守儿童不陷入生存的困境或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国家有义务为基层组织的此项监督工作提供人力、财力和物力,保障基层组织有能力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留守儿童生存权法律保护的事中监督措施
留守儿童的生存权是极易遭受侵害的。对于已经陷入生存困境的留守儿童,国家应及时介入,要求留守儿童的父母承担抚养、照料和监护的责任。如果留守儿童父的母拒绝或联系不上留守儿童的父母,则国家应该将处于生存困境的留守儿童交由合适第三方(留守儿童亲属或社会抚养机构)抚养或监护,国家财政预先支付此项费用。通过进行训诫或采取法律措施使留守儿童的父母履行保障留守儿童生存的职责,并偿还国家先前预支的费用。国家介入家庭生活的此项权力应交于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或民政部门,以防止此项权力过度干预家庭生活而侵害公民的家庭自治。
(三)留守儿童生存权法律保护的事后救济措施
在留守儿童的生存权确已遭受侵害,或虽未遭受侵害但已陷入生存困境,且父母无能力进行事后救济的情况下,国家对此类留守儿童应予以救济。国家应制定儿童普惠性福利政策,对留守儿童的生存权予以特别保障,确保留守儿童的生命、健康、安全和生活不再受到二次侵害并能恢复到完满状态。
对于故意忽视或侵害留守儿童生存权的父母要有惩罚措施,依情节严重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在“贵州毕节四兄妹服毒自杀”事件中,父母对四兄妹的死亡负有严重的监护失职责任,事件中的父亲常年在外,对留守儿童生存的故意忽视,已经构成对儿童生存权的不作为,在法律上应予以制裁。事件中的母亲离家出走多年,对四个儿女不管不顾,有遗弃之嫌,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结语
对留守儿童生存权予以法律保护,还只是解决留守儿童生存问题在法律层面上的努力。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的生存问题,既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大力帮扶,更需要国家积极采取有效的保障措施。这就要求我们去努力建构完善的儿童权利保护法律体系和儿童福利保障体系,从制度上和措施上共同保护留守儿童生存的权利。留守儿童的生存权有了保障,才能实现其个体发展的自由和平等,促进儿童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秋香.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困境与对策[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3-4.
[2]孙玉娜,孙玉艳.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杂志,2007,(7):2084-2086.
[3][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M].林浩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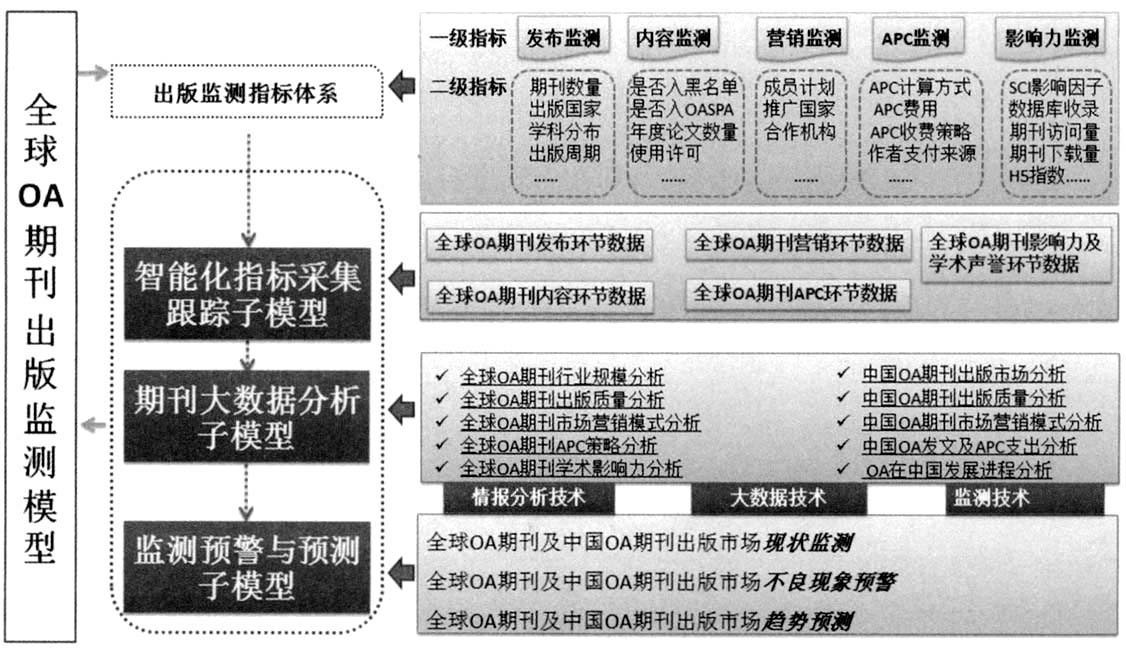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