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教育学的主题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变化,但教育学的核心问题、基本问题则始终未变,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始终不断地反思,我们需要与前人进行不断的对话。今天教育学的学术建构尤其应回到教育学的经典思想之中。我们需要树立“大教育学”的观念,不应仅仅停留于所谓纯粹的教育学典籍,而是将目光投向所有凝聚着教育思想与智慧的典籍中去。随着教育学学术性的确立,教育学学科发展需要我们重新明确教育学的学科视阈,并着力在实践关怀的同时进行学术性的重新建构。
关键词:教育学;学科视阈;学术建构;实践关怀
在我们的日常及专业用语中,“教育学”有时指一门单独的学科,有时指一组以教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当指一门单独的学科时,它典型地体现在一些经典的教育学着作与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往往以“教育学”或“教育原理”命名)中,尽管它似乎缺乏一套较为严谨的理论体系及较为统整的逻辑架构以及相对独特的概念体系、理论与方法,但每一位经历过较为系统的教育学学术训练或以此为业的人往往都会或隐约或清晰地感受到,教育学有一种独特的关怀,尽管在既有的理论中它时隐时现,但或许正是它,才是这样一门学科在整个学术知识体系中的安身立命之本。
我国的教育学发展到今天,需要对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进行系统地反思,也需要探讨教育学理论形态的重建。从“学科”的视野审视教育理论本身,这将有助于确定教育学这样一门学科今后的发展方向。
一、人类知识领域中“学科”的意涵
“学科”的较为宽泛的含义是指知识的门类,在学校教育体系的课程设置中,它往往与具体的“科目”相等同。在人类知识领域中,尤其是在现代专业研究领域中,“学科”则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及更为严格的规定。
现代学术体系源自西方,追寻“学科”在西方学术体系中的发展脉络可以使我们对其意涵有更为清晰的把握。
“学科(discipline)”的字源探究显示出它种种意义的历史衍延,多于能够为它立下确实定义。……古拉丁文disciplina本身已兼有知识(知识体系)及权力(孩童纪律、军纪)之义。乔塞(Chaucer)时代的英文discipline指各门知识,尤其是医学、法律和神学这些新兴大学里的“高等部门”。据《牛津英语字典》,discipline(学科/规训)为门徒和学者所属,而教义(doctrine)则为博士和教师所有。结果“学科/规训”跟实习或练习关联,而教义则属抽象理论。有了这个分立,就能理解何以会选取“学科”来描述基于经验方法和诉诸客观性的新学科。称一个研究范围为一门“学科”,即是说它并非只是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Discipline亦指寺院的规矩,以后则指军队和学校的训练方法。此二义之错综关联显示在一门知识中受教,即是受规训而最终具备纪律,亦即拥有能够自主自持的素质[1]13。
称一门知识为一学科,标志着其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地位的确立。“学科”一词持久使用,也标示着知识的组织和生产的历史特殊性。人类知识的分门分科是由来已久之事。自古典时期伊始,西方知识的学科划分主要体现为哲学(包括逻辑、伦理和物理)及中世纪的“七艺”(包括文法、修辞、辩证法和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类的知识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世纪末自然哲学断裂成为各门独立自然科学,现代诸学科始正式诞生。社会科学稍后从道德哲学中分裂出来。“人文科学”是20世纪对那些遭排拒在自然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现代哲学是由科学形成时清除出来的东西界定的,其他现代人文科学则首先以古典语文学的形式出现,其后衍生出历史、现代语言甚至艺术史。19世纪现代学科的涌现,全赖17和18世纪新建制和新践行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变革可算是科学学会的形成。学会的成立标志了知识划分史上的突破[1]16。
综观人类知识领域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学科是历史的产物,并以一定的措辞建构起来,每一门学科需要确立其相对明确与清晰的边界,学科的划分循着几条线索进行:研究对象、方法、理论、认识论上的预设和意识形态[1]30,与这种学科划分内在标准的明晰相并行的专业研究队伍的形成及相关建制的确立。诚如一位研究大学的史学者所说,“学科首先是一个以具有正当资格的研究者为中心的研究社群,各个体为了利于互相交流和对他们的研究工作设立一定程度的权威标准,组成了这个社群。”[2]29与一门学科的确立相关的建制有:专业组织、专业刊物、专业基金,或许还包括在大学中设置相应的专业与课程。正如福柯所说,“学科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它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而在这种同一性中,规则被永久性地恢复了活动”[3]224。
二、教育学的学科认同
在人类历史上,教育学思想源远流长,如同人类的文化一样古老。在现代学术知识体系中,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也早已确立了起来,这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赫尔巴特、康德乃至17世纪的夸美纽斯。
然而,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教育学的学科地位似乎并不高,并时常处于学科认同危机之中。美国的霍斯金曾这样描述教育学在西方学术体系中的学科困境,“‘教育学’不是一门学科。今天,即使是把教育视为一门学科的想法,也会使人感到不安和难堪。‘教育学’是一种次等学科,把其他‘真正’的学科共冶一炉,所以在其他严谨的学术同僚眼中,根本不屑一顾。在讨论学科问题的真正学术着作当中,你不会找到‘教育学’这一项目”。“多年来‘教育学’已逐渐接受屈居次等学科的地位。19世纪末叶,教育才作为一种现代的专门学术领域发展,也许一度有别的发展可能。可是,当年那些教育领域内响当当的任务,如巴黎的教育法教授涂尔干,芝加哥的杜威,都已被社会学和哲学这些“真正”的学科吸纳过去。自此以后,多年以来,普通人(尤其是政客和商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教育专家。教育实践的方式愈来愈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接受改造和进行实验,但教育学却无法找到一种显示出其学科地位的声音去作出回应”[4]43-44。
作为一名教育学研究者,我们有时会感到激情满怀,隐约会感受到这样一门学科之学科使命的召唤,这种学科使命是难以被其他所谓“正统”学科所取代的,有时则会感到一种深深的不安,因为不论是在学术领域中还是在现实情境中,我们时常会处于一种“失语”的境地,我们似乎难以确立起自己的学科话语体系与学科立场。对教育学的学科认同的确充斥着这种内在的不安与张力。
从人类的思想文化史及现实的教育实践来说,教育学的确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正如李泽厚所说,教育学必将是人类未来的“皇冠”学科。这种对教育学的宏愿的确可以坚定我们的教育学信念,但现实中的教育学学科状况却的确不容乐观。
从作为一门学科的外在相关建制的角度来说,教育学在当今我国的专业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已毋庸置疑,已形成了数量相当可观的研究队伍,已成立了自己的专业研究组织(学会),已拥有了为数不少的专业刊物乃至专业出版机构,已建立了各级专业基金(课题)管理机构,在大学中也早已设置了相应的专业与课程。然而这种外在的繁荣并不能掩饰内在的学科认同困境,随着学科的发展,我们需要不断地对此进行深入地反思。
教育学的这种学科认同困境有时甚至导致有人主张将教育学这门学科予以消解,宣称教育学的终结,并代之以教育学科群。但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并不能与教育学科群相互指代,否则,人类独特的教育学关怀(即对人的成长的关怀)及曾经赋予这门学科的期待与使命将无由担当,人类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教育学思想与文化也无由维继,缺乏了教育学这门核心学科凝聚与支撑的教育学科群也将整合并将彻底沦为其他学科的“殖民地”或失掉理论的根基。
教育学这种学科认同的困境,更多是来自于自身“同一性”的危机,这涉及到其对象、方法、理论及学科立场等诸多方面。今天的教育学正面临着系统的理论重建,需要对这些问题在新的学科视野中进行深入的反思。
三、教育学的学科视阈
每一门真正独立而又成熟的学科都有其所关注的独特的核心问题域。例如经济学所关注的是资源稀缺问题,政治学所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至善问题,社会学所关注的是社会的构成与运行问题。那么,教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域是什么呢?无疑理应是如何助人成长问题。这种核心问题域显示了每门学科独特的关怀,是该学科在人类知识领域中安身立命之本,它也承载着人们对这样一门学科最基本的期待。一门学科的理论论述围绕其核心问题域展开,从而形成其基本的理论理路,这种理论理路体现在一门学科的经典着作之中。然而,由于教育学理论的逻辑架构相对较弱,这种理论理路极容易发生迷失,从而沦为其他学科话语的“跑马场”与“殖民地”,因而需要我们有对教育学学科视阈的自觉。
当前教育理论研究所出现的理论理路含混与迷失现象,与对“教育学”这一学科概念内涵的把握不无关系。“教育学”顾名思义乃为“教育之学”,但我们日常及学术研究中所用“教育”一词事实上有两种含义:一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教育现象”,一为“助人成长的教育行为”,由此,所谓“教育学”也就具有两种含义:一为“研究教育现象的学问”,一为“探讨如何助人成长的学问”,对于前者而言,教育现象作为一种研究的对象与领域,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对之具有普遍的解释力,而对于后者而言,一般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则在相当程度上无能为力,这当为教育学的自身独特领地所在。[5]
运用一般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或者说人类现象)的教育现象”进行研究并做出理论解释本身并无可厚非,并且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但这本身并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学研究”,更不能成为教育研究的全部。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学研究当为“助人成长之学”,正是在这里存在着教育学不同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领域的独特的理论理路。法国社会学家、教育学家涂尔干曾试图将“教育科学”与“教育学”区别出来,认为前者是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教育进行科学研究,而后者则主要指向引导教育行为的价值与理念探寻[6],这种划分是颇有道理的。加拿大教育学者范梅南曾形象地说过,“教育学就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7]18,可谓点出了教育学的真谛。
赫尔巴特使教育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他认为,“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就是学生的可塑性”。[8]207“或者接受宿命论,或者接受先验主义关于自由的观念的各种哲学体系,其本身都是排斥教育学的,因为它们都不可能毫无疑义地接受这种显示由不定型向定型过渡的可塑性的概念”[8]20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学不同于哲学,“(哲学)在他们得势的时候早就霸占了一切高雅的领域,而他们迄今几乎只对于那种看起来似乎卑微的儿童世界不去触动”[8]11。杜威曾使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发生了扭转,认为真正的哲学应是教育哲学。
当前,在我国的大多数教育学着作或教科书中,都大致将教育学界定为“研究教育现象并揭示其规律的学科”,这样一种学科界定太过宽泛,而极容易将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与“教育科学”或“教育学科群”相混同,而忽视了教育学乃“助人成长之学”的应有之义。事实上,在这些着作中,对“教育”概念的界定都是从“助人成长的活动”的角度而言的(例如,将“教育”定义为“有目的、有意识地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发展的实践活动”),而对“教育学”的界定却由此偏离开来,泛化为“研究教育现象”。由此进一步导致了整个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游离与泛化,泛化为主要探讨教育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之间的关系的这样一些本应由“教育科学”探讨的“大”问题,以及教育制度、课程与教学等这样一些本应由教育分支学科探讨的具体问题。而对于自身本应探讨的核心问题域及学科关怀则发生了迷失。
由此,我们需要在对教育学的核心问题域明确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教育学所理应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始终处于人类千百年来所积累起来的教育学思想的核心层面,也始终是人类教育实践所要面对的一些根本问题,它们理应居于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层面。这些基本问题大致包括:第一,教育的存在性意义。包括,教育之于人的根本意义,教育与人性的关系等。第二,教育的条件与机制。主要探讨教育促进发展的原理与层面。包括教育者的教育爱、教育期待、教育理解,以及学习者的意向等。第三,教育的实践。包括教育的场景、情境、教育实践的发生与改变等。第四,素养教育,旨在探讨人生所需基本素养及其教育培养。这些问题是人类教育所要面临的一些永恒性问题,也是作为“助人成长之学”的教育学所应探讨的一些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可能由其他学科所完全取代,而是教育学的固有领地。
四、教育学的学术建构
一门学科的学术性强弱决定着其在整个学术知识领域中地位的高低。一般来说,一门学科的学术性主要是就厚重的理论基础、规范的理论话语以及严谨的治学方式而言的。学术性不能被等同于科学性,“科学性”往往是就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态度而言的,往往更偏重于实证性,更多地运用于自然科学或实证科学领域,而“学术性”则更多地侧重于本学科的理论积淀、承继与创新,更多地存在于人文社会研究领域。
由于教育问题与社会的时代精神之间似乎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因而教育学极容易成为时代精神之学。诚如涂尔干所说,“正是这种处境,催生出种种夸大、偏颇、片面的教育理论,表现的只是应一时之需和热情一阵的愿望。这样的理论无论如何都不会长久,因为它们很快就会产生出其他理论来矫正、补充和改造它们。……我们需要去理解的,不是属于自己的时刻的人,不是被我们感受时处在某个特定时点的人,也不是像我们一样受一时的需要和激情所影响的人,而是处在贯穿时间的整体性当中的人”[9]15。
近年来随着社会流行话题及主流学术话语主题的变换,教育理论研究也在不断变换着自身的主题,诸如主体性、主体间性、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可持续发展、信息化、全球化等等,成为教育学研究的一个接一个的热点问题,然而未等弄清这些理论探讨究竟对教育实践产生了多大影响便又切换了主题。近几年来,有关后现代的理论又扑面而来,大有让人目不暇接之感。因为迷失了自身的理论关怀,很多教育学研究只能处于“跟风”之中,跟“主流学术话语”之风,跟“流行社会话题”之风。这难道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教育学研究吗?
教育学并非不应去关注时代精神,相反,教育学注定与时代精神之间存在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因为教育是在面向新时代培养人,新教育理想的建构必定立基于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基础之上。但仅仅关注时代精神并非是教育学研究的全部,否则,整个教育学研究必将会流于轻薄。相反,真正的教育学需要有其厚重的学术根基。那么,今天的教育学应如何考虑其学术性建构?
教育学的学术性建构应立基于对其核心问题域及基本问题的关照,立基于人类千百年来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教育思想智慧以及经典的教育学着作,立基于审慎严谨而又恢弘博大的研究心态。
尽管教育学的表面主题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变化,但教育学的核心问题、基本问题则始终未变,人类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沿着历史的轨迹缓慢前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始终不断的反思,而前人既有的见解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启示,我们只有在洞察前人已达到的思想深度与高度的基础上才能超越前人,我们需要与前人进行不断地对话。教育学的理论理路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能得以逐渐明确。
我们今天教育学的学术建构尤其应回到教育学的经典思想之中。在这里,我们需要树立“大教育学”的观念,即目光不应仅仅停留于所谓纯粹的教育学典籍,而是将目光投向所有凝聚着教育思想与智慧的典籍中去。例如,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饱含着浓厚的教育思想与智慧(有一位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家曾说过“儒学本质上是一种教育学”),其中有待我们去汲取与继承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
五、教育学的实践关怀
对教育学学术性的强调并非意味着忽视其实践性,教育学理论始终是以教育实践为旨归的,并且从根本意义上讲,它也只能来源于教育实践。
在人类整个知识体系之中,教育学最大的特点或许就在于它与实践之间的紧密关联。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几乎教育学的所有问题都是来源于教育实践的,而非来自书本的演绎,教育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即教育实践的根本问题;二,教育实践中的经验与智慧是教育学理论的源泉;三,真正有建树的教育学理论必定需要有相应的实践建构形态相伴随。
教育学的学术性与实践性并不矛盾,因为有深度的思想必定会带来明智而一贯的行动。人类的教育实践始终面临着一些永恒的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学术智慧的照亮,一些经典教育思想的魅力也正在于其永恒的当下性。
教育学的经典思想与智慧需要结合当今教育实践的特点予以重新阐发与发展。
康德曾经说过,“人们可以把两种发明看作是对人类来说最困难的东西,这就是统治艺术和教育艺术,而且人们对它们的理念还处在争论之中”[10]7。从这样一句话中,我们也可以体认到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所要承担的重负与使命。
参考文献
[1]沙姆韦,梅瑟-达维多.学科规训制度导论[M]∥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北京:三联书店,1999.
[2]Geiger,Roger.To Advance Knowledge:The Growth of the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1900—194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3]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Discourse on Language,New York:Pantheon,1972.
[4]霍斯金.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意想不到的逆转[M]∥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北京:三联书店,1999.
[5]王有升.理论理路的分歧与借鉴——哲学社会科学语境中的教育学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9).
[6]爱弥尔.涂尔干.教育与社会学[M].沈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7]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M].李树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8]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M].李其龙,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9]爱弥尔.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M].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0]伊曼努尔.康德.论教育学[M].赵鹏,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更多教育论文,请关注一起问道论文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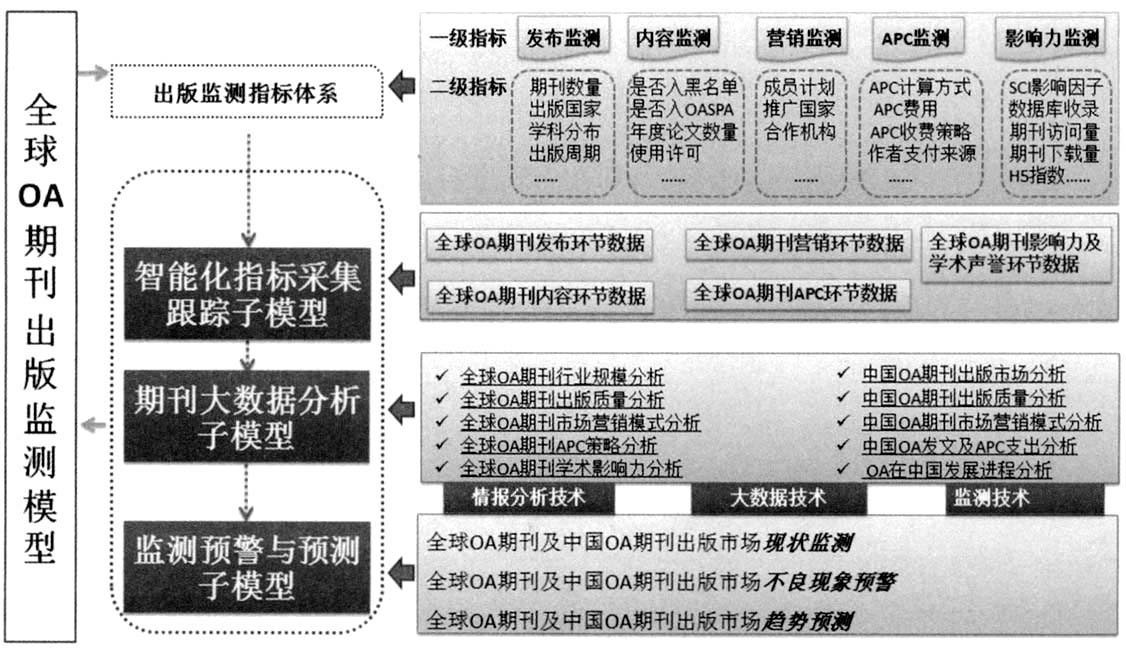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