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新生的德意志共和国的民主宪法(史称“魏玛宪法”)颁布还不到三年之际,年轻的宪法学家施米特就发表了《政治的神学:主权学说四论》。在紧接着发表的小册子《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一九二三)中,施米特宣称,如果“要科学地研究民主政制”,就“必须从一个我称之为政治神学的特殊方面入手”(第一章结尾)。按照这个提示,《政治的神学:主权学说四论》的论旨与德意志共和国颁布的民主宪法有关,是试图“科学地研究民主政制”的法理学尝试。然而,民主政制与“政治神学”有何相干,或者,民主政制与何种“政治神学”相干,这样的问题在当时乃至后来的大半个世纪里都晦暗不明。
在民主政制据说已经成为“普世价值”的今天,还有必要“科学地研究民主政制”吗?反过来问也行:民主政制是一种科学的设计吗?如今,即便提出这样的问题,已经会让人不安,甚至招来“主义”志士的愤怒訾议。尽管如此,在当今西方学界声誉如日中天的意大利学者阿冈本(GiorgioAgamben)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承接施米特的法理学尝试,力图从“政治神学的特殊方面入手”“科学地研究民主政制”:一九九八年,阿冈本发表了让他声名鹊起的《法外人:主权与裸露的生命》(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五年后又发表了《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一书。显然,这两本书的书名都与施米特的《政治的神学:主权学说四论》的开篇名言相关:“主权就是决断例外状态。”在二○一一年出版的《王国与荣耀:为了一种经世和统治的神学谱系学》(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For a TheologicalGenealogy of Economy and Government)一书中,阿冈本宣称,他要更深入地推进自己在十多年前展开的这一研究取向。
如何更深入地推进从“政治神学的特殊方面入手”“科学地研究民主政制”?阿冈本承认,他指的是从深入研究佩特森与施米特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七○年间的那场关于“政治神学”的历史性争论入手。《政治的神学:主权学说四论》发表之后,施米特当时在波恩大学的同事和好友、新教的教会史—教义史家佩特森对施米特的“政治神学”这一提法及其与民主政制的品质问题的关系非常感兴趣。
佩特森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早期基督教会的圣餐论,他所具有的早期基督教神学文史功夫,使得他能够把民主政制与“政治神学”的相干性问题变成一个切实的论题,从而写下了一系列短制之作或研究草案。然而,纳粹上台之后,佩特森突然改变立场,因应《政治的神学:主权学说四论》第二次印刷(一九三四),发表了反对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的小书:《作为政治问题的一神论:论罗马帝国中的政治神学史》(Der Monotheismus als politisches Problem: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der politischen Theologie im Imperium Romanum,1935)。在序言中,佩特森试图首先澄清自己的研究与施米特的论旨的相似和不相似之处。据阿冈本的看法,佩特森的澄清堪称公允。因为,佩特森认为,把基督教信仰的上帝观说成一神论是错的:基督徒信仰的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而非独一的神—把基督教信仰的上帝观说成一神论,是近代启蒙思想的伪造。对于原初的基督徒来说,他们的上帝信仰超越了犹太教的一神论和希腊的多神论。基于这一根本性的认识,佩特森否认现代民主政制的品质与古老的基督教“政治神学”有相干性,并宣布自己的这本书“终结”了基督教政治神学的“神学可能性”
问题—与此同时,佩特森力图通过自己的早期神学史研究反过来证明,现代民主政制的品质倒是与一神论的政治神学相干。
对于佩特森的反戈一击,施米特直到三十多年之后的一九六八年才做出反应—在《政治的神学续篇》的序言中施米特这样写道:蒲鲁东一类的无神论者、巴枯宁一类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孔德一类的实证主义者早就宣称,科学已经终结了所有政治的神学—这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佩特森这样的“极其虔诚的基督教神学家”也如此宣称……阿冈本认为,无论施米特还是佩特森,在这场论争中其实都没有把要说的话挑明,他的《王国与荣耀》许诺要把施米特,尤其佩特森藏着掖着很深的东西挑明。于是,《王国与荣耀》花了不少篇幅来讨论佩特森与施米特关于“政治神学”的论争,尤其试图深入考察佩特森关于东罗马帝国初期的政治神学与帝国建制关系的论述。
阿冈本是否看准了这场的确堪称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论争的实质要点,后文再说,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他发掘这场早已过去的论争的意图。据阿冈本自己声称,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西方的经世权力问题,尤其是现代民主政制的起源问题。阿冈本承认,在他之前的研究典范是福柯的权力谱系学。然而,在他看来,福柯的权力谱系学尽管曾风靡一时,实际上最终半途而废。究其原因,福柯的权力谱系学仅仅基于近代的启蒙政治论,并未触及基督教诞生之初的政治神学。
如果要彻底搞清楚西方现代民主政制的权力谱系学,就得追溯到早期基督教神学的三位一体的经世论。阿冈本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权力需要荣耀?为什么统治需要典礼、欢呼和礼仪?
这一提问仍然来自施米特的问题提法: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施米特就曾提出,民主政制通过人民向领袖欢呼来证明其自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后来有人据此攻击施米特,说他的这一论点无异于是在为希特勒政权提供正当性论证,因为这个政权当初获得过人民的欢呼。
如果这种指责成立的话,施米特就不是在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要科学地研究民主政制”,而是在为一党制或极权主义做论证—然而,这种指责同时也将表明:迄今所有民选总统都是希特勒式的,因为,如今所有代议制的民选总统在竞选时无不首先谋求选民的欢呼—竞选成功之后也都有这样一个仪式:噙着泪花面对向他欢呼的民众发表感言……阿冈本这样的头脑认识到,不仅僭主式的民主政制需要对权力的欢呼和荣耀,代议式的民主政制也离不了对权力的欢呼和荣耀。
更进一步说,民主政制仍然需要传统政制那样的对权力的欢呼和荣耀,但与传统政制不同,在民主政制的语境中,要拥有对权力的欢呼和荣耀就得操控公共意见或传媒。由此可以说,施米特提出民主政制通过人民向领袖欢呼来证明其自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是一个“科学的”论断,他力图搞清的是现代民主政制的一般法理性质,而非在为某一种民主政制提供正当性论证。
就佩特森与施米特的论争本身而言,阿冈本更看重佩特森的“政治神学”研究。在他看来,施米特关注的是现代民主政治如何可能在世俗意义之中来建立起统治的正当性,佩特森的“政治神学”研究则更关注政治统治的仪式,这就为阿冈本自己所要关注的所谓“公共实践”的语源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因此,在《王国与荣耀》中,阿冈本花了不少工夫来思辨佩特森的“政治神学”研究所展示的真正的基督教政治—即仪式和三位一体教义与权力建构的关系。用阿冈本自己的话来说,这意味着将政治建立在参与到赞美天使和圣徒的膜拜之中—佩特森的早期基督教政治神学研究表明:作为仪式行为的政治其实是对末世荣耀的文化参与。阿冈本断言,在佩特森看来,从世界大战到极权主义,从技术革命到原子弹,所有这些事件均表明,现代民主政制的法理中是否有基督教神学因素,其实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政治统治离不了仪式行为。换言之,通过细嚼佩特森的历史“政治神学”研究,阿冈本力图从中抽取出一种普遍的政治权力形式:欢呼和荣耀。阿冈本对佩特森—施米特论争的关注带有明显的福柯—德里达式的后现代精神立场—也就是关注政治权力与自然生命的紧张关系:发表《王国与荣耀》两年之后,阿冈本又推出了《最高的贫困:修院规矩与生命之形式》(The Highest Poverty: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2013)。阿冈本的关切使得他未必能够看到佩特森—施米特论争的实质问题所在,因为,施米特的“政治的神学”问题提法要揭示的不过是,看似世俗化的现代民主政制仍然具有神学性质。如所周知,西方现代民主政制是在与基督教神权王政的统治权威的斗争中生发出来的。然而,现代民主政制尽管宣称拒斥神的权威,其实仍然需要类似于神的权威。佩特森在纳粹政变之后反对“政治神学”的提法,的确意在抵制僭主式民主制的类似于神的权威。例如,在写于一九三六年的题为《作为帝王的基督》一文中,佩特森指出,应当把《新约·约翰启示录》中的基督形象理解为与罗马皇帝相对立的形象。这意味着,基督神性的“帝王”地位取消了世间统治者让人敬拜自己的资格,也取消了他们建立不受限制的统治的资格。
显然,佩特森希望让基督徒的“帝王崇拜”与现实中的“帝王崇拜”区别开来,进而让基督教神学与可能为僭主式民主制的正当性提供神学论证的企图撇清关系。施米特在一九六八年对佩特森的回复力图指明,佩特森在一九三五年提出的批评并未切中问题的要害—这个要害就是:政治统治的品质是否真的能够无需任何形式的神性权威要素。公允地看,佩特森作为神学家更关心僭主式民主制的品质与一神论政治神学的相干性,施米特作为法学家更关心的是,任何形式的民主政制都离不开独一神式的决断。现代西方政治理论让人仅仅在僭主式民主制与代议式民主制之间选择,本身就大有问题。
显然,这样的问题与阿冈本所关切的权力谱系学问题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这样一来,阿冈本对佩特森—施米特论争的理解就难免偏离论争的问题方向:政治统治本身是否具有神性权威要素这一政治法理问题,变成了西方政制与基督教神学的关系问题。
由于有了这些限制,阿冈本的研究以发掘佩特森—施米特论争为基础,反倒使得他深化权力谱系学研究的企图可能会落空。毕竟,政治统治本身是否具有或是否应该具有神性权威的问题,并非是在基督教会神学及其与帝国政制发生关系之后才出现的,柏拉图的临终大着《法义》开篇就挑明了法制的神性权威问题。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的临终场景,今人甚至可以读到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虽然这话出自柏拉图笔下的刻贝斯之口—他对苏格拉底说:不过嘛,苏格拉底,如果我们这会儿说得有道理的话,亦即,神看护着我们,我们是神的所有物,你刚才说,热爱智慧的人们兴许容易愿意去死,就显得荒谬啦。因为,[要说]最为明智的人们离开自己侍奉[神的地方]不感到懊恼,就没道理啦,毕竟,在这里,诸神作为最优秀的万物主管者照管着他们[这些最为明智的人们]。最明智的人恐怕不至于会认为,自己一旦变得自由将会更好地受到看护罢。没脑筋的世人反倒或许会这样认为,即必须逃离主子,甚至兴许不会算计一下,不应该逃离好人,而是应该尽量待在[好人]身边,因此,才会不动脑筋地要逃离。有脑筋的人会渴望一直待在比自己更好的人身边。(柏拉图:《蒲法伊东》,62c10-e3)民主政制的根本法理之一就是:不要“主子”,人民自己做主—不用说,对于这样的法理,几乎没有谁会反对或觉得不对。毕竟,谁都愿意做“主子”而非当奴仆。可是,即便代议式民主制的民选总统仍然是“主子”,他的责任和义务仍然是照管好自己的选民。政治统治的实质没有变,变的是“主子”的品质:现代民主政治理论追求的并非是作为“好人”的“主子”,而是合意的“主子”。
话说回来,由于阿冈本的影响,佩特森这样一位相当学究的教会史专家如今也开始受到一般学人关注,毕竟是件有益的事情。就在《王国与荣耀》问世那年,佩特森的《神学论集》(TheologicalTractates)英译本问世,收入佩特森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七年间的神学文章和草稿—这显然得归功于阿冈本对佩特森的关注。不过,佩特森的《神学论集》英译本没有收入佩特森讲疏《新约·约翰启示录》讲稿,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严格来讲,佩特森的政治神学的思想史意义,并非在于阿冈本的视野范围,而在于这样一个更重要的文明史范围:罗马帝国首都东迁之后,东方正教神学与帝制建构的关系,迄今仍是西方政治理论界的一大盲点。毕竟,罗马帝国并没有随着帝国西部陷入日耳曼蛮族之手而灭亡,而是继续存活了近千年之久。佩特森的罗马帝国政治神学研究必然会使得以帝国西部的政制嬗变以及奥古斯丁的政治神学为主导的西方政治思想史面临巨大挑战,对此我们汉语学界难道会不愿意乐观其成?
更多政治思想史论文,请关注一起问道论文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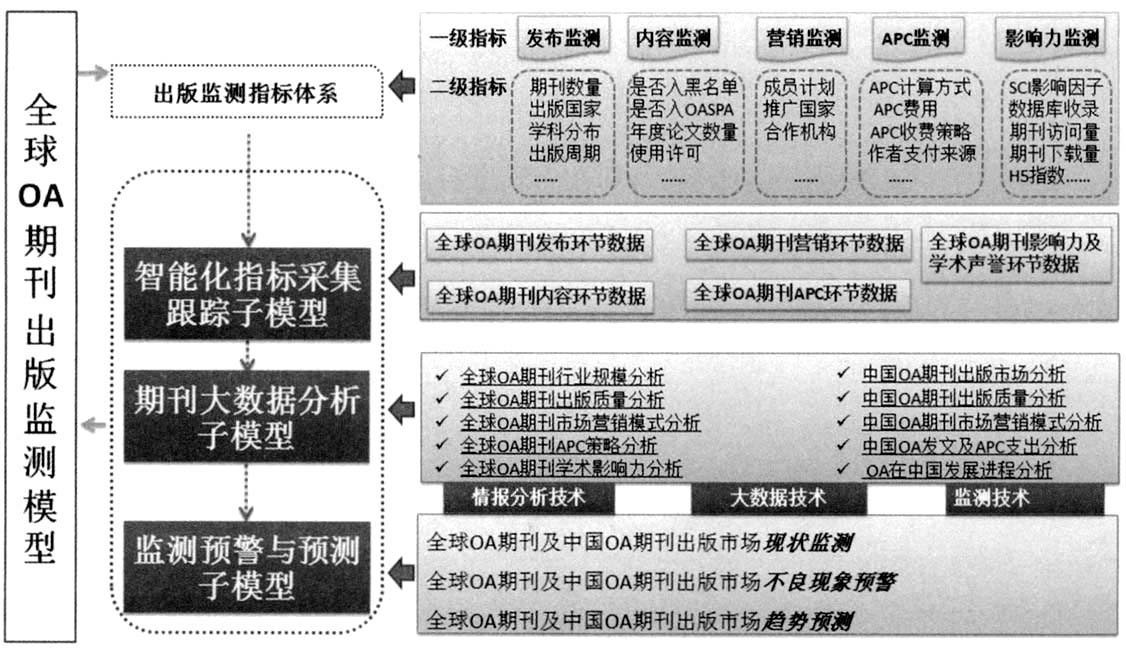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