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时期的考古发现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资料。最近《中国文物报》发表《河北崇礼太子城发现一处金代行宫遗址》一文(见本报2017年12月15日《文物考古》周刊),这是最新也是考古发现后很快就见诸报端的考古成果报告,值得赞许,笔者深表敬意!
这篇报告介绍了河北省各相关文物考古部门在张家口市崇礼区四台嘴乡太子城村南调查时发现一座古代城址,读过后受益匪浅。但报告的最后结论是:“太子城遗址时代为金代中后期,约金世宗(1161-1189年)、金章宗(1190-1208年)时期。”并进一步说:“由上可以推测,太子城遗址的性质为金代皇室行宫遗址。”“故太子城有可能即《金史》中记载金章宗驻夏的泰和宫。”笔者认为:将太子城村城址的年代定为金代是不符合实际的,从目前的报道看,定为金代中后期皇帝行宫没有任何证据。因此,该文所确定的城址年代和其性质的这个结论,值得商榷。
笔者认为:崇礼太子城村古城址,应该为辽代城址,而非金代城址,更非金代皇帝行宫遗址。现将笔者意见,就报告所示材料,逐项试析于后。
报告说太子城村城址的年代为金代,并且是皇帝行宫,理由之一是:“位置重要,太子城位于金中都与金皇室驻夏点金莲川之间的驿道上。”此言亦误。金莲川,原名曷里浒东川,今称闪电河,为自南向北流在河北省与内蒙古自治区间的一条河,是滦河上游的西源,流经沽源与正蓝旗等地。金大定八年(1168年)以曷里浒东川遍生金莲花,遂改名为“金莲川”。此地在金中都(今北京)之北,如从金中都去金莲川,在两地之间横亘着自东北向西南走向的大马群山脉,道途险阻,群山迎路,无驿道相通,只有沽河(今称白河)至沽源的谷道所经,是为坦途,其山脉在此间中断,地势缓平,南北可通,从今北京走延庆经赤城到沽源至正蓝旗,然后即可到达金莲川,这是一条直道。古代如此,至今交通虽发达,其路仍是这样,而这条路是不经崇礼太子城的。崇礼太子城建在群山中,四周都是山,并无坦途,没有驿路。如果从金中都去金莲川,应是北走,而若是去太子城,则须向西北走,这样不仅路远,且是进入大马群山的西段山区,到太子城后又须转向东北行,则又是走进群山之中,不只是舍近求远问题,而是并无驿路,因此由太子城到达金莲川是比较困难的。应该说,金代皇帝去避暑,本是求安逸舒适,焉能有驿道不走,却要窜于乱山间?崇礼,在金代属西京路宣德州,位置偏西,但若由中都至金莲川,直北走奉圣州,而不必远绕太子城,这是很明显的。故称太子城在“金中都与金皇室驻夏点金莲川之间的驿道上”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了。
再看报告所述的第二个理由是:城址“规模较小,辽金城址规模一般为府级周20里,州级8-10里,县级及以下6里,太子城3里,面积较小。”由此规定,太子城既然不是州、县城,就考虑它是皇帝的行宫城址了。这种用里数大小规范古代城址为某级建置的说法,未免有些机械了。笔者从事文物考古工作至今六十多年,在各地调查不同时期的城址有数百座,其实并无像报告所说的这种情况:必须是多少里,才是某级建置。其实城垣大小,是由当时各种原因和条件决定的,形状、大小等并非有硬性规定和形制千篇一律的约束。实际根据我的考古调查所见,所有城址几乎各不相同,难以复制,那种“州城8-10里,县级及以下6里”就是一个不符合实际而自我设定的命题,其实在辽金时期,没有几个州、县城,在建之前是先有定制然后遵照这个里数进行建造的,不许越制!此事可参见已发表的各地辽金城址的考古调查报告,另有已出版的北方各省、市、区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文字部分所记载的辽金城址概况,也都记录颇全,其里数俱无定制,皆可验看。因此,报告认为“太子城3里,面积较小”,不是设定的州、县城的里数条件,于是就定为“行宫遗址”,这个理由是说不通的。
其三,根据报告介绍城址中遗物出土的情况是:“太子城遗址出土遗物以各类泥质灰陶胎的筒板瓦、龙凤形脊饰、迦棱(陵)频伽等建筑构件为主,另有部分筒板瓦、脊饰等。除建筑构件外,还出土部分白釉印花、刻花碗盘,粉青釉盒、碗,黑釉鸡腿瓶等瓷器残片及木结构建筑上的铺首、门钉、鎏金铜片等铜铁构件。建筑构件中有大量勾纹方砖、素面条砖上戳印‘内’‘宫’‘官’字,白釉瓷器中已发现15件印摩羯纹碗盘底有‘尚食局’款铭文,另出土2件铜鎏金的小龙头饰件。从出土遗物分析,太子城遗址时代为金代中后期,约金世宗(1161-1189年)、金章宗(1190-1208年)时期。”从报道所述出土遗物看,它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基本都是辽代而非金代。如各类泥质灰陶胎筒板瓦、龙凤形脊饰、迦陵频伽纹等建筑构件,这些都具有辽代特点,我们常见的辽代筒板瓦,一般均为泥质灰陶胎,体较大而厚重,颜色正灰,火候较高,其滴水瓦头为大沿宽边,饰各种花纹,瓦当更为明确,特点突出,上述遗物在辽代城址和遗址中随处可见;龙凤纹脊饰,更是辽代独有的建筑饰件,此前发表的考古发现材料不少,皆可为证。笔者往年在各地辽代城址、遗址的调查中,在建筑址上也发现不少这种遗物,至今仍保存有相当数量的照片;如果再提到迦陵频伽纹,则更非辽莫属,这种纹饰是随着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其形人首鸟身,迦陵频伽意为“好音鸟”,但金代佛教式微,此种纹饰不被采用,而辽代则不同,佛教之盛,上至皇帝下至庶民,无不信奉,当年寺院林立,至今辽塔遍地,《辽史》记载“一日祝发三千,饭僧十万”,可见其盛况,于是今天在辽代考古中,不仅在建筑饰件上而且在大量的铜器、玉器等生活用品或装饰品上常见这种纹饰,就是铜镜上也以此为镜背的花纹。再如瓷器有黑釉鸡腿瓶,这种瓶式更为陶瓷界和考古界公认的辽代遗物,由于辽金时代契丹与女真的民族生活方式不同,鸡冠壶、鸡腿瓶、海棠盘等为辽代契丹族的典型、代表性的瓷器,这是人所共知,而为金代所无的。再如“建筑构件中有大量勾(沟)纹方砖”,沟纹砖是学术界公认的辽代典型遗物,而不是金代砖的特点。辽代砖一般较厚重,其上有戳印和手掌痕者,在考古发现中时常遇到,而金代就很罕见了。特别要说的是“白釉瓷器中已发现15件印摩羯纹碗盘底有‘尚食局’款铭文”的问题,此则更趋明显。首先说“摩羯纹”饰,它本就不是金代瓷器特有的纹饰,而恰为定窑早期即五代和北宋以及辽代瓷器所乐于采用的装饰纹样,这为过去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瓷器鉴藏所确定,已无疑义,不必深辨。其次说“尚食局”款问题,根据过去的考古发现,这种划款瓷器在定窑遗址中有出土,是在北宋地层里,冯先铭先生曾介绍过。对于这种划款瓷器,我曾写过《“官”和“新官”款瓷器之研究》一文,在综合所有相关的瓷器后,发现它们都是出土于早期属于五代、辽和北宋时期的遗址、墓葬、塔基、窑址中,而没有在较晚的遗存中发现,因其后已不再流行这种表示特种含义的划款作法了,现在学术界都认同这一事实惰况,而太子城中出土15件划“尚食局”款的白瓷,正好是说明太子城的年代为辽而非金,由瓷器的专属性而得到证明。
第四,金灭辽后,金代在建置上,基本上是沿用辽宋旧置,不仅未有更多创建,而是对原有建置作了很多省并。就以辽代地域来说,金代对辽的建置省、废的非常多,只要对照《辽史·地理志》与《金史·地理志》就会发现,辽代州、县金时除沿用一些外,其余很多州、县或废或省并或降等,实际金代自行建置的并不多。如果认为太子城是金代建的话,崇礼地域在辽时属西京道,金为西京路宣德州,金代皇帝自中都路去金莲川避暑,没有必要远去西京路宣德州地域建行宫,若建也应在奉圣州,但作为直接通道的奉圣州却没有其遗存,其事就值得考虑了。
第五,考古调查或发掘在得出年代结论时,应以该处的遗迹结构和出土遗物自身特征为准,由遗物说话,以此定遗迹的年代。但太子城村城址出土的遗物中,没有特征明显的金代遗物,更没有文字材料,也没有纪年文物,如何能判断其为金代的?反倒是辽代特点非常突出,如报道中所列举的那些遗物,只能说明它是辽代的。
报道认为太子城址是金中后期的,即金世宗至金章宗时,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更不可能了,因章宗后26年金就亡国了!一个直到晚期几乎历经金之全盛期的城址,在经过仔细调查和大面积发掘后却未发现较为典型的金代遗物,也无年代明确的遗物,更无表明是皇家的遗物,定为金代的行宫城扯,尚欠充足的理由和实物的依据。
因此,根据上述意见,笔者认为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太子城村古城址为辽代城址,而非金代城址,更不是金代中后期的皇帝行宫遗址。
(作者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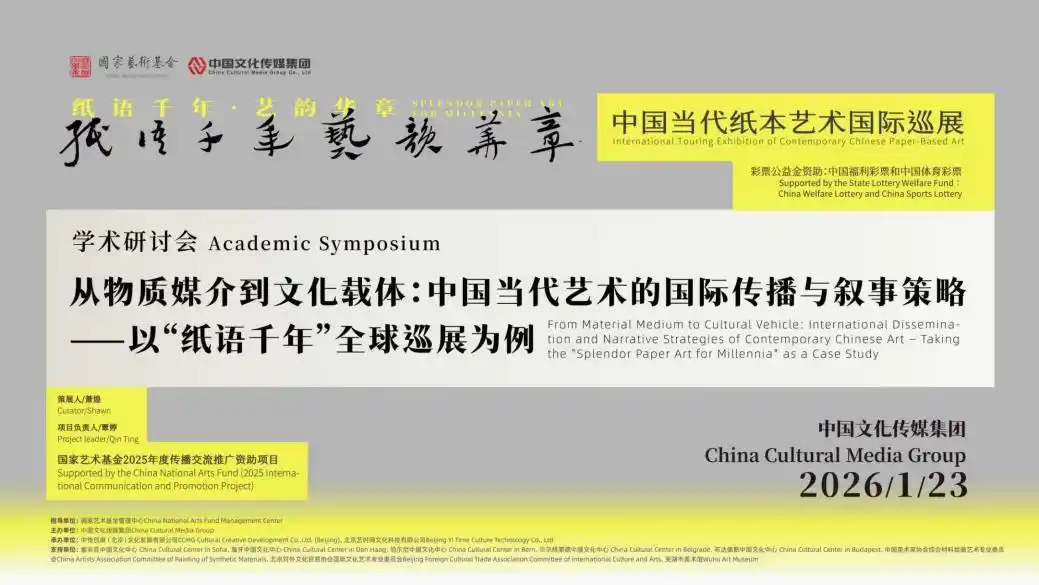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