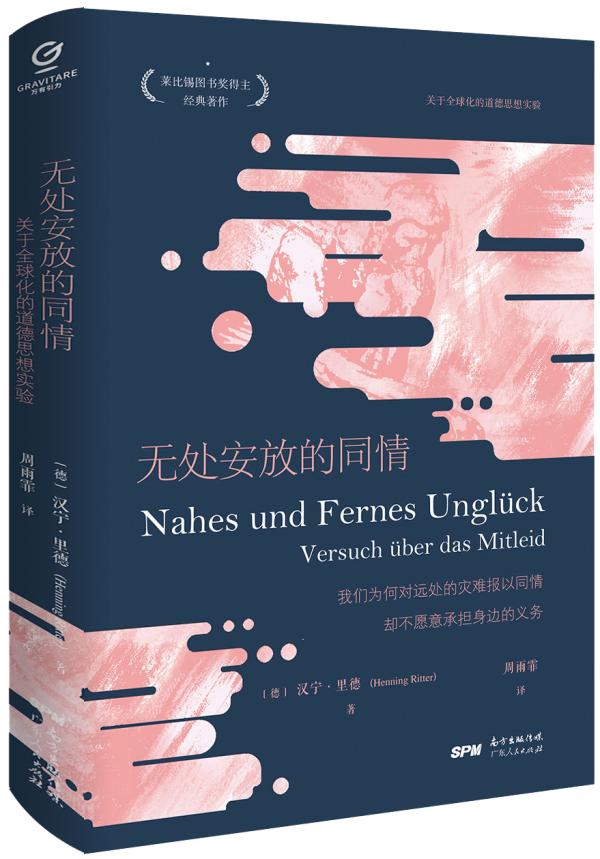
《无处安放的同情:关于全球化的道德思想实验》,[德]汉宁·里德著,周雨霏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即出,220页,58.00元
“在每个周五的下午,当我到了咖啡店时,汉宁·里德(Henning Ritter)总是已经在那儿了。我在门口稍作逗留,好仔细观察他。他埋首于文稿中,全神贯注,像是有个无形的罩子将他与四周的人隔绝开来。他的手中握着支铅笔,他的阅读总是立即转化成批注和评论。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看到我,露出那特有的诙谐坏笑。”2013年6月23日,六十九岁的汉宁·里德因病在柏林去世后,他的友人、法兰克福作家马丁·莫泽巴赫(Matin Mosebach)如此回忆道。
汉宁·里德生于1943年的西里西亚,父亲为明斯特的哲学家约阿希姆·里德(Joachim Ritter)。他曾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艺术史、哲学与古典学,翻译出版卢梭作品集,在六七十年代西柏林的知识分子圈子里颇为活跃。虽然汉宁·里德没有选择从事学术研究,甚至未取得学位(除了汉堡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但这并未妨碍他成为文字考究的旧式学人,欧洲人文思想中独具品位的漫游者(Flaneur)。与其父亲不同,汉宁·里德的作品从不追求体系化的思想构建,他的作品以流动思维中屡屡出现的闪光点而著称。作家莱纳尔德·戈茨(Rainald Goetz)曾在《明镜周刊》撰文评论道:“汉宁·里德的思索来源于文本,产生于他与古典思想家的对话之中。进入这场对话的读者将在阅读的过程中自己抵达答案、质疑、矛盾,当然最好是与作者达成认同。(中略)里德的文风在追求写作的另一种原始功能,这就是捕捉跳跃着的思维过程。里德收集起那些灵光一现、那些闪烁在思维之聚散离合中的无数个顿悟的瞬间,接着以诡辩的方式使这些偶尔迸出的思想火花变得通俗易懂。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的‘自我’看似是消失了。”
作为非学院派的散文家、媒体人与思考者,汉宁·里德在作家、人文学者及各式知识分子之间交友甚广。1985年,他成为法兰克福汇报文艺副刊《人文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版块的责任编辑,到2008年退休的二十多年里将该版块耕耘成一块现代媒体中已十分罕见的、充满了古典人文气质的园地。除了《无处安放的同情》,里德本人的主要作品包括《长影子》(1992)《东河岸边的楼群风景:我们这个时代的遗产》(2000)《笔记本》(2010)《伤者的嚎叫:关于残酷的讨论》(2013)。其中《笔记本》获得2011年的莱比锡书展奖。
《无处安放的同情》的德文原版早在2003年就已问世。当时正值红绿联盟政府的执政艰难期,长期的经济低迷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成为德国媒体最关注的话题。欧洲难民危机尚未发生,其所激活的一些传统道德哲学问题,譬如道德的对象应如何界定、如何界定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我们”与该共同体之外的“他者”,在德语公共圈内亦未引起广泛争论。汉宁·里德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正在对传统的道德情感产生一些不可逆的作用。同情和共感,原本是人们对身边的、近旁的同胞所抱有的情感。当全球化使世界变得看似越来越小,当传媒技术足以将灾难的现场在视觉和听觉上带到我们身边,当世界各地发生的不幸都能够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时,人们是否会对不相识的他者产生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式的同情呢?而这种看似普世的同情心,将指引人们走向无边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一种抽象的伪道德,不指向任何具体的道德行为,最终让人们在伦理方面成为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呢?
《无处安放的同情》即是汉宁·里德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的思索。里德指引读者进入十八世纪的思想世界——这是欧洲社会迈入近代初期,各种道德信念随着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开始互相碰撞、相互作用的时期。通过援引古典哲学家们关于道德之有效范围的争论,里德将穿越时间与空间的文本连同其产生的背景一同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与作者其他的作品类似,本书并非旨在通过系统性的分析来论证具体的观点,而更像是一系列围绕着同一个论题展开、相互之间关联较为松散的哲学随笔集。第一部《杀死满大人》,以巴尔扎克《高老头》中主人公拉斯蒂涅与友人毕安训之间的一段对话开场。拉斯蒂涅问,若单凭使用意念就可杀死一位远在北京的满大人并因此致富,是否值得试试看呢?以经典文本为分析对象,通过追溯这一桥段在启蒙以来的欧洲思想史中以千变万化的姿态被反复引用的谱系,里德发现,围绕着道德感、同情心之射程的论争最早发生在启蒙哲人之间。
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哲人主张,人应当致力于这样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升华,让陌生、遥远处发生的灾祸与降临在邻人亲友身上的不幸一样震撼他们的内心。卢梭则持相反意见。基于自然法的道德传统,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只能在与人的现实交往中获得道德感觉;对陌生他者的道德责任感,并非源于人的自然状态,而是通过教化习得。众所周知,对于自然社会、自然感情通过规训、制度化逐渐走向“文明”的叙事,后期卢梭抱有十分怀疑与消极的态度。他警惕对“文明”的笃信与对普世人性的盲目乐观,并暗示毁灭的种子恰恰就埋藏在文明社会的高歌猛进之中。卢梭对进步主义的嘲讽、对经济合理主义的批判、对文明及其命运的怀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重新浮出水面。弗洛伊德援用满大人的桥段——虽然弗氏对“自然状态”的认识与卢梭大相径庭——来表明他对文明进程的认识:文明发展的逻辑中孕育着倒退的危机。
第二部《道德的地理学》爬梳了十六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哲人们围绕着“是否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普世道德”这一问题所展开的思考。大航海时代让欧洲人有机会去探索地图上未知的地区,带回关于异域的见闻。其中各种光怪陆离的习惯与礼俗引发人们对身边习以为常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相对化,同时追问,不同的地理空间中运行着的,究竟是不同的真理,还是真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一问题意识在法哲学思想中的分歧,体现为伏尔泰在处理卡拉事件时标榜普世正义,呼唤一个覆盖全人类的法庭;而贝卡里亚等人则主张,法律与道德具有地理上的局限性,换言之,当犯罪行为触犯了某地的公共安全,理应由该地的司法机关来进行量刑。这就离卡尔·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中提出的边界理论(amity lines)不远了:和平、契约、规范与睦邻关系仅仅在边界的这一边有效,越过边界则进入了不法之地。任何一位熟悉德国思想界的读者,对里德与这位“危险的心灵”之间维持多年的忘年友谊都不会陌生。通过援引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关于自然风貌塑造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决定个人意识情感的论述,里德含蓄地对施米特提出的二分法进行了呼应:一条边界割裂了欧洲与欧洲以外(尤其是新世界),区分了法制的空间与法外之地。
第三部《遥望远处的灾难》以1755年发生在里斯本的一场大地震开篇。这场灾难震撼了整个欧洲,促使知识精英们开始集中思考这样一组问题:当听说这座欧洲大都会里的数万人瞬间在地震中丧命,人们还要为了自己身上微不足道的疾患耿耿于怀吗?远在欧洲其他城市的居民应当以何种姿态来面对里斯本的悲剧,才算是符合仁义道德呢?伏尔泰以此次地震为契机,开始了他对天命主义者的讨伐。伏尔泰洞察到,欧洲其他城市的住民对发生在里斯本的悲剧感到恐慌,正因为他们在事件中感受到一种关于存在的不安:里斯本的命运时刻有可能降临到自己身上。相对于在伏尔泰身上过少的着墨,里德花费大量篇幅讨论亚当·斯密对于类似问题的回应。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一名与中国毫无贸易往来和利益瓜葛的善良的伦敦人,当他听到这个巨大帝国连同亿万居民被地震吞没时,他首先感到震动,不久后便化为对人生无常的感慨,然后一切回归平常。讽刺的是,如果这名伦敦人在睡前得知自己将失去一根小手指,他会彻夜难眠,惶恐不安。里德发现,斯密塑造伦敦人这一形象,实际在隐秘地回应狄德罗关于自然权利的辞条中对于“残暴的思考者”的描述。在这一部分中,里德通过耗费大量篇幅追溯斯密对情感逻辑与行为逻辑的区分,传达了他对同时代的博爱主义者的警告:看似高尚的同情心,如果无法与援助受害者的具体行为建立联系,就仅仅是一种“矫揉造作的悲痛”而已。
第四部《塞住两耳的哲学家》以卢梭《第二论文》中一个段落的真实作者为悬念,通过揭示隐藏在卢梭与百科全书派学人(主要是狄德罗)文本中的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呈现了二者对人性抱有的截然相反的理解。在《第二论文》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物:当哲学家听到可怜的人在他窗子底下哀嚎,他扯了扯睡帽来遮住自己的耳朵。事后,在《忏悔录》《对话录》以及给圣日耳曼先生的信件中,卢梭一口咬定这一残酷的形象并非源自自己笔下,而是狄德罗的加笔。卢梭对这一形象的否定,与他对“自然人”的赞美直接相关:卢梭认为,目睹受苦的生命而涌出怜悯心,是人类以及动物的本能。捂住耳朵的哲学家正是因了过度深思熟虑,理智压倒了他本能的同情心,阻止了他对窗下那名可怜人施救。卢梭由此继续推演到,理性与思辨或许能够使我们在抽象的层面体察到遥远处的人们所遭受的不幸,却使我们逐渐失去意愿和能力,对眼下、对身边的现实中受苦的人们伸出援手。里德对卢梭的仰慕由来已久。早在1978年,里德就编译了一套卢梭著作集(上下二册)以及卢梭书信集一册,2012年再次编译出版卢梭哲学书信集一册,可以说对卢梭思想的倾倒几乎贯穿里德的整个创作生涯。或许里德对卢梭极端的主张“沉思的人是一种变了质的动物”持保留态度,但卢梭对同时代哲学狂热主义的警告无疑让里德感到不安:当启蒙所带来的对理性和进步的信仰无往不利地取代了作为偏见与盲信的宗教狂热主义,理性主义本身已处于变成另一种盲信的危机。
在本书中,里德对进步主义、辉格史观的警觉,对启蒙及其困境的反思随处可见。从卢梭对即将到来的“革命的世纪”之预言,到弗洛伊德与其同时代人对“文明的进程必须经历倒退与回归”的共识,里德似乎在暗示,对人类道德日益进步、人权意识日臻完善的近代主义式的盲信不过是一种虚妄的幻想。屡屡当这种傲慢的妄想被鼓吹到极致,人类就离灾难不远了。里德也敏锐地捕捉到,当上一次灾难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对“政治正确”近乎道德洁癖式的坚持似乎与理性主义在十八世纪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取代了不久前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全体主义,成为不容置疑的新宗教。与此同时,过于迅猛的全球化重新激活了一个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业已出现过的道德问题:对于那些发生在自己的家门、国门外,甚至万里之外的灾难,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否应当感同身受呢?
在他突然离世之前,里德曾向《观念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Ideengeschichte)的特集“保守主义美学”寄稿一篇题为“德国式的事物”(Deutsche Dinge)的散文,对基民盟政权在欧元危机中的处理政策,尤其是希腊拯救方案提出异议。里德认为,当代历史研究(Zeitgeschichte)作为战后德国公共圈中支配性的话语,通过将“记忆的塑造”置于“还原史实”之上,不断地再生产关于赎罪的神话,同时向公众进行道德使命的说教。这种对于“责任能力”(Schuldfähigkeit,汉斯·布鲁门伯格语)近乎痴迷的追求使得德国在欧洲面临二战后最严重的危机时,所扮演的掌舵人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道德令式(moral imperative)。在文章的结尾,里德援用胡戈·冯·霍夫曼史塔(Hugo von Hoffmannsthal)对道德教化之反作用的嘲讽,如此写道:“德国人对德性过分的强调,正是非道德的根源。当有那么一天,道德教化的力量枯竭,等待着人们的,除了卷土重来的非道,还能有什么?在今天的德国,人们明显能观察到道德的疲软无力化:道德仅存在于公共领域,在每一个个人的生活中,它已失去了分量。”(Henning Ritter,“Deutsche Dinge”,Zeitschrift für Ideengeschichte,Heft VII/3,Herbst 2013,p.57)
里德去世后仅两年,欧洲大陆面临的道德危机之紧迫性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5年9月,叙利亚男孩艾伦·科迪伏尸海滩的照片在欧洲各大媒体揭载,拷问着这片大陆上每一个拥有政治参与权的人,在面对难民潮时要采取何种姿态。至2017年底,德国实施开放边境政策以来入境的难民达到一百万人以上。同时,欧洲境内“文明的冲突”亦在升级。仅在2016年一年,情节恶劣的恐怖事件在欧洲此起彼伏:3月22日,布鲁塞尔连环爆炸案造成三十二人死亡;7月14日,一辆货车在尼斯冲撞庆祝国庆的人群,造成至少八十余人丧生;一周后,慕尼黑奥林匹亚购物中心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九人死亡;12月19日,卡车袭击柏林夏洛滕堡区的圣诞市场,致十二死五十六伤。在面临欧元危机、难民危机以及全球化带来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对身份认同的不安时,德国选民做出的选择应该不会让里德感到意外:在2017年9月的德国大选中,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得到百分之十二点六的选票,一跃成为德国第三大党,也是战后第一个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极右翼政党。
显而易见,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强制性的普世主义,给欧洲的自我认同与自我主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保守主义者的回应,来自欧洲各国的十名保守主义学者在2017年10月7日发布连署声明《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A Europe We Can Believe In),其中有数个主张与本书的主旨不谋而合。比如其中屡屡提到的关键词“一个虚假的欧洲”。声明称,这个虚假的欧洲“把自己歌颂为一个普世共同体的先驱,但事实上,它既谈不上普世,更称不上是一个共同体”。此外,“虚假欧洲的支持者受惑于一种对进步的必然性的迷信。他们相信历史站在他们一边,这种信念使其变得傲慢和轻蔑,也没有能力去承认他们正在建构的所谓‘后民族’‘后文化’的世界存在着各种缺陷”。在里德看来,百科全书派学人所构想的日趋大同的世界正是这样一个“虚假的欧洲”:盲信进步、盲信普世价值与仁爱,盲信人能够通过思考与道德提升将人性之纽带扩展到全世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里德格外关注的、卢梭对理性狂热主义的警告在《巴黎声明》中也得到了体现。第二十四条“我们必须抵制假造的宗教”正是在抨击启蒙负的遗产给今天的欧洲带来的灾难:“普世主义者以及虚假欧洲的普世化自负,暴露了这是一种假造的宗教事业,包含着强烈的教义承诺——以及革出教门。这是一种有效的麻醉剂,使欧洲作为一个政治体陷入麻痹无力。我们必须坚持,宗教渴望适存于宗教的领域,而非政治的领域,更不用说官僚行政领域。为了恢复我们政治和历史的能动性,欧洲公共生活的再世俗化是势在必行的。”
里德在本书中要表达的核心思想与《巴黎声明》的异曲同工并非巧合。签署声明的唯一一名德国学者罗伯特·施佩曼(Robert Spaemann)正是约阿希姆·里德的弟子和明斯特学者圈子中重要的天主教哲学家。如果将本书同时置于欧洲保守主义思想谱系以及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给后冷战时期的欧洲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这两个维度内,读者不难认识到,本书中的思索正是一名文化保守派学人对中间偏左的主流公共圈冷静而委婉的问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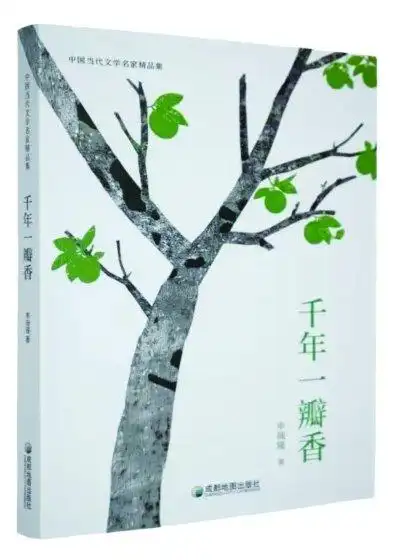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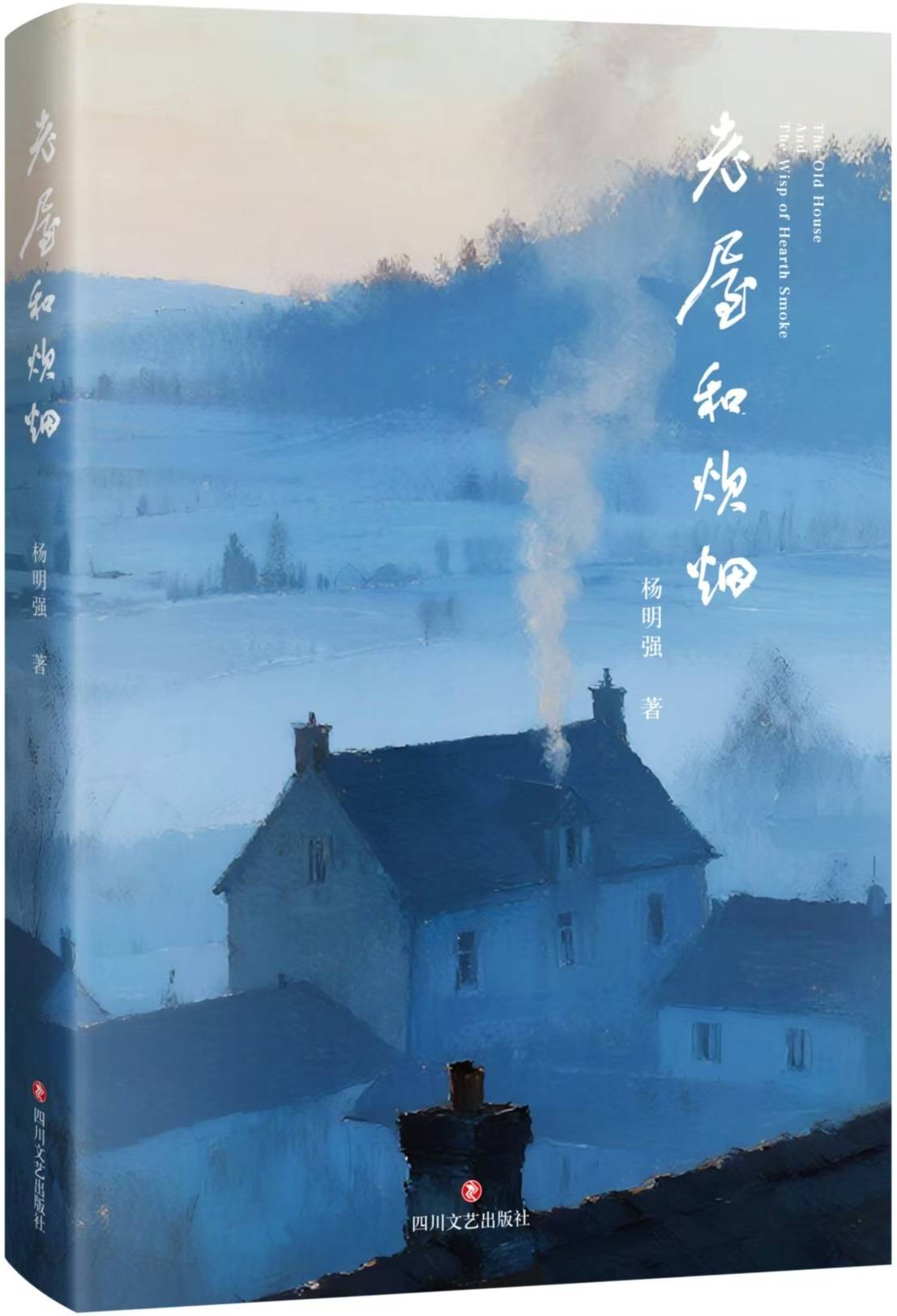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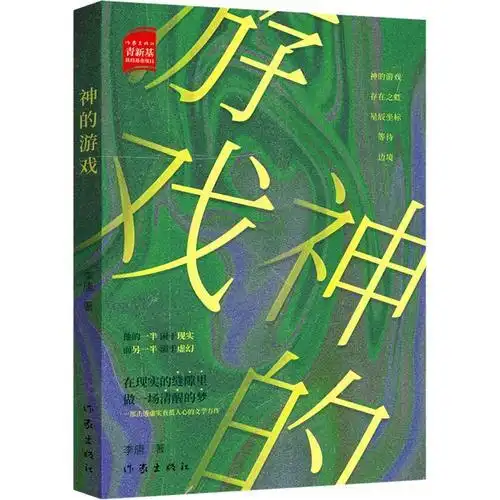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