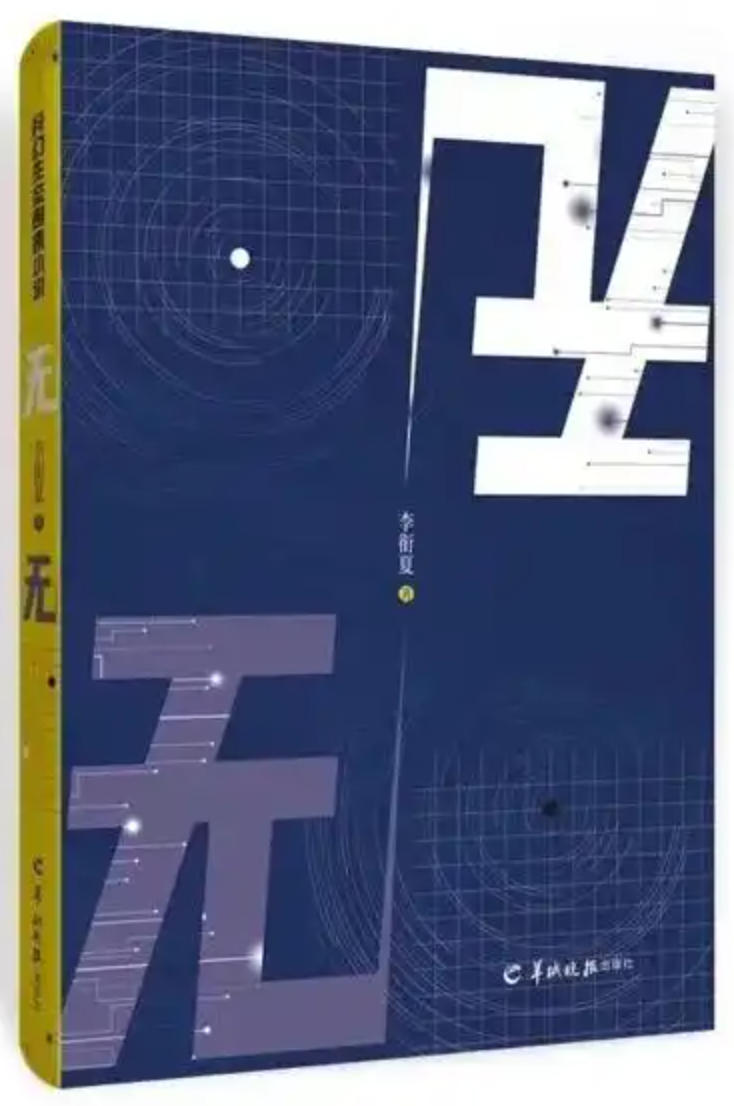
《无无》是李衔夏的长篇科幻代表作,这部作品从语言、思想、艺术手法到内容,全方位突破了传统文学的边界,开创性地劈开了一块新高地,开出一片哲学之花来。初读时,我以为这是科幻小说,后来坚定地相信,这绝不仅仅是科幻,而是人类的集体哲学思辨,是生与死的极致追问,是现实主义的超凡体验,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小说。读完后,我不禁惊呼:小说竟然可以这样写!
李衔夏勇于从自身寻求突围,将大量刺破传统、挑战庸常思维的句子打水花一样甩出去,一浪接着一浪。语言是李衔夏的秘钥,他借此抵达了他心中神秘的地方,也造成了一种语言的刺破感和新鲜感,让人感到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宝藏还在前面等着挖掘,而不像阅读传统小说,看了上一节猜出下一节,或者看了这一句,就知道下一句。这就使得这部小说下沉到非常深邃的海底——作家似乎在挑读者了,他只为能读懂的那部分剖开心怀。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据说这本书被退稿四次,原因是《无无》着实艰深难懂。我想,作家把这些小插曲写在书的后记里,应该是释怀了。
李衔夏在小说中搭建了一个庞大的哲学对话场域。主人公夏元贞身份复杂,既是演员,又是诗人,还是击败了世界冠军的围棋黑马——其实她真正的身份是哲学家。她爱前夫李红兵,爱前夫捐赠精子生下来的儿子李蘩祁,爱李呈悲,有过一些不可控的瞬间,她还爱上了她的舞伴或者一些微不足道的人或机器人——其实她真正的身份是无数的你、我、他。
读惯了平常的小说,会被他“离经叛道”的敢下笔惊吓到。当他写到“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们和我们自己结婚”时,传统文学中泾渭分明的角色边界轰然倒塌。但绝不是哗众取宠——打破,重组,重组,打破,只有身份、情绪、状态被一一打破,思维才能进入“无”的境界,天马行空,抵达哲学的自由。
李衔夏不断从《道德经》《易经》《易传》《庄子》《文始真经》等作品里拆解、汲取真知灼见,无数次推出主题“无无”(无无即三,三生万物),又用《鹖冠子》“美恶相饰,命曰复周;物极则反,命曰环流”来破解,然后不断地陷入“矛盾—破解—矛盾—破解”的哲学循环。老子、庄子、黑格尔、苏格拉底、海德格尔、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他们忙碌地穿梭在文本中,却毫无违和感。
他像进入了一款升级打怪的哲学游戏,当发现了一个新观点,尚未被这个观点所折服,马上又看到另一面,于是,矛盾—对立—对立—矛盾,不断螺旋式上升,最终将整本书推向了浩瀚广博的思想之海。与其说这是小说,不如说这是大型的辩论圆台,无数尖锐的思维在此碰撞出火花,让读者大呼过瘾。
《无无》最具革命性的艺术特征在于其彻底摒弃了传统意义上的对白,全文无一句对白。这种“无对白”设定不是形式主义的炫技,而是一种全新的“留白”,是对交流本质的深层叩问。作者将传统小说依赖的对话功能分解到其他叙事元素中,这就使得,反而文本中处处都是“对白”——思想的交锋、博弈,矛盾的对立、和解,每一处都可以是正与反的交流。
诚然,这样写是冒险的,但他如入无人之境,竭尽所能去阐述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机器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不断地加强叙事者作为人的声音。这些声音,并不会比庸常的“对白”更弱,反而有一种更高的真实和更为自由的“交谈”——引领读者不断去思考,去超越,去质疑,去辩驳,这比任何的“对白”都来得更加有力和掷地有声。
《无无》的颠覆性不仅在于其形式与内容的创新,还在于它重新定义了文学与思辨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无》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份关于文学创新可能性的宣言书——当所有边界都被打破,“无”即是孕育万“有”的子宫。
李衔夏以《无无》证明了文学在形式与思想层面仍有无限可能,其创作犹如在文学边界的刀锋上起舞——伤口是勇者的勋章,而舞姿本身已构成对平庸最优雅的背叛。这部作品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它的“不同流”:那些未能被理解的裂缝,恰好为未来文学的生长留下了光照进来的空间。
(作者原名朱晓敏,系河源市十佳青年,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化馆第四批特聘创作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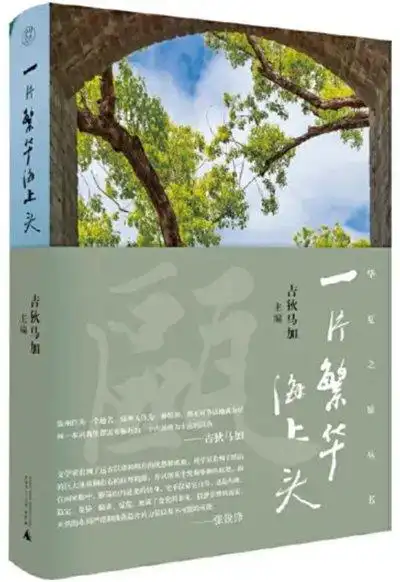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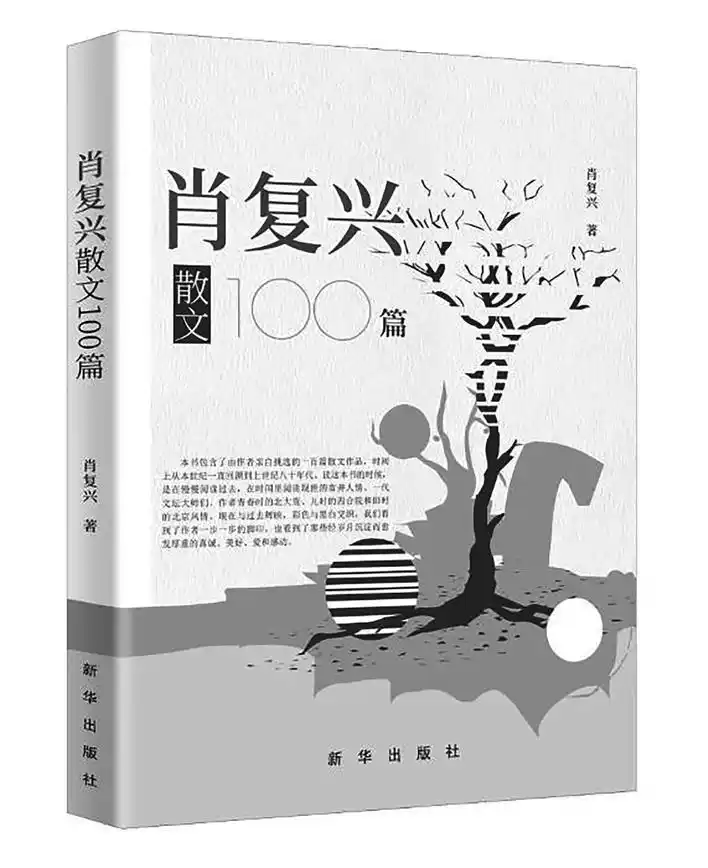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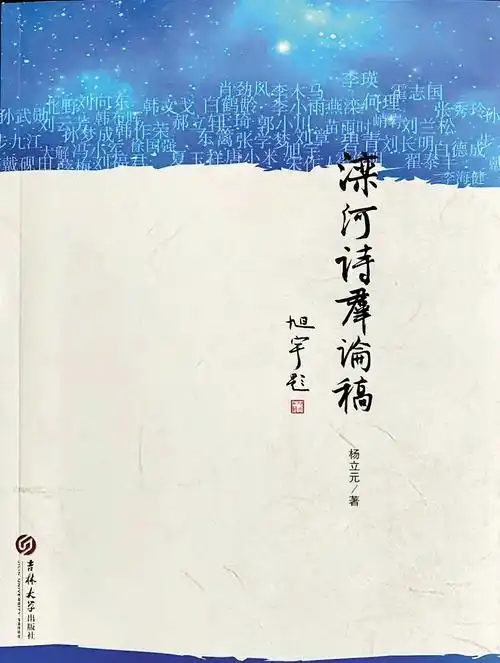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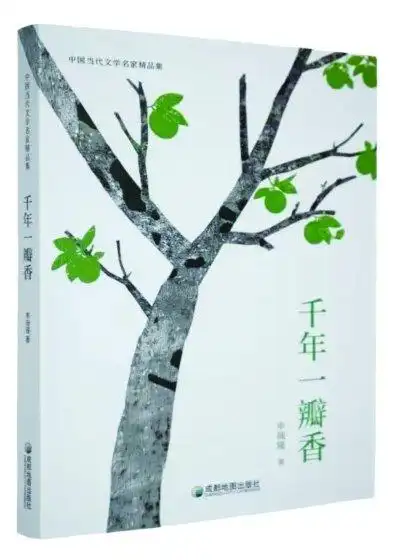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