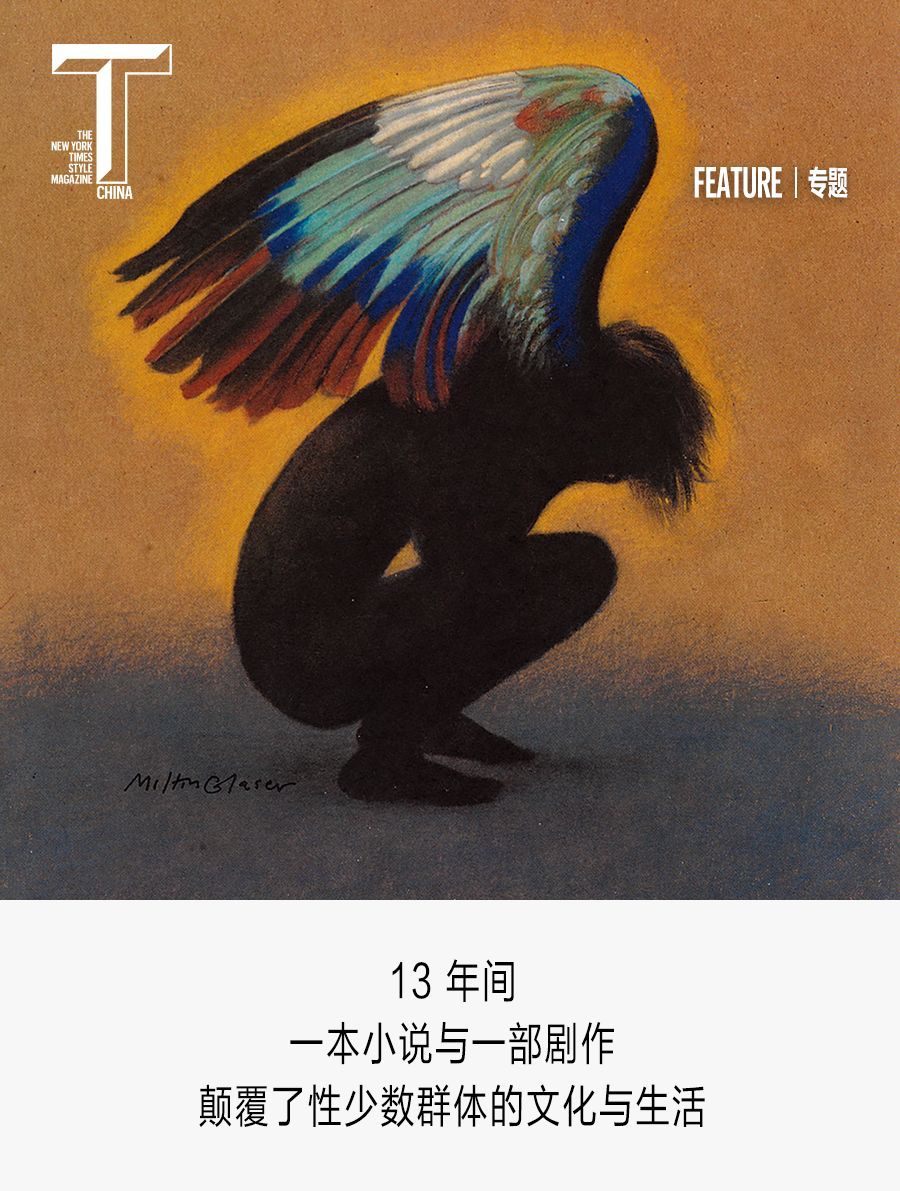
Andrew Holleran 于 1978 年出版的小说《Dancer From the Dance》(暂无中文译名,以下简称《Dancer》)并非我读过的第一部同性文学作品,但却是第一本「街头巷尾人人传阅」的同志小说。至少,我身边的男同性恋都对它青睐有加。
用今天的话形容,这是同性文学的首个高光时刻。
虽然它讲述的是主角 Malone 和 Sutherland 的故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 20 世纪 70 年代纽约同志群体的生存状态。这是一个关于每周六天,甚至夜夜起舞的故事,是一个在公园、公共浴室、密室等任意场合干柴烈火的故事,也是一个除了泳裤和墨镜外,两手空空地在火岛(Fire Island)欢度周末的故事。
Andrew Holleran 小说《Dancer From the Dance》(1978)初版封面
青春、美貌、金钱、毒品,各种元素一应俱全。故事开始了。
更重要的是,《Dancer》 描绘了男同性恋者的未来。他们告别了家庭,越过花园的白色篱栅,与一群奇妙之人为伍。在他们构想中,曼哈顿岛将成为一片流光溢彩的新天地,而曼哈顿也将挣脱原始的道德约束,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是的,Holleran 笔下的纽约自由而辉煌 —— 直到一切都荡然无存。如今,对有些人而言,(他们一度想要逃离的)带前廊和花坛的房子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可恶了。
最终,Malone 和 Sutherland 收获了一场悲剧。在那个年代,人们秉持这样一种观点:男同性恋可以乘坐公交车,但抵达终点站之前,一定要把他们赶下去。
这意味着,Malone 与 Sutherland 终其一生都在漂泊。他们的死更像是《哈姆雷特》中的 Ophelia,而非 Tennessee Williams 笔下的 Sebastian Venable,丧命于乱刀之下,又被乡下的野孩子分食。
对于《Dancer》,有人爱不释手,有人不以为然,围绕其价值的争议一直不绝于耳。它算不算严肃文学?还是说,因为它回应了我们的人生,我们才「希望」它是严肃文学?在时代悲剧下,Malone 和 Sutherland 真的是悲剧人物吗?又或许,他们无足轻重?
《Clemens 与 Jens 在我巴黎住宅的门厅里相拥》(2001 年),摄影师 Nan Goldin 作品。随着艾滋病的爆发,同性文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本小说如实地展现了同性恋世界的某个「小圈子」里(漂亮的白人小伙)放浪形骸的洒脱人生。1970 年代中后期,狂欢正在上演。Holleran 不仅是描写这场狂欢的开山鼻祖,也记录了这场狂欢是如何将读者抛向高空,像掏空万圣节的南瓜一样把他们掏空,再扔到某个秋意盎然的海滩。
只不过,当年的我们无从知晓,在所有描绘这场狂欢的作品中,《Dancer》是一声绝响。三年后的 1981 年,首例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Gay 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GRID)的病例出现了。
但疾病的流行并未终结纵欲享乐或吸毒成性的生活。同性恋对芳华、美色与物质的渴望依旧不减。与此同时,GRID 这位初来乍到的「客人」正兀自站在角落偷笑,无声地玷污着此刻的氛围。
1981 年起,冲击接踵而至,但没有什么比 GRID 更引人注目。到 1985 年,已经有大约 8000 人死于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征),同年,里根总统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了这个词。在新药试验协定方面,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进展十分缓慢,艾滋病患者纷纷请愿,并表示,愿意承担所有副作用引发的风险,因为他们明白,如果坐以待毙,自己将活不过两年 —— 而最严重的副作用,莫过于死亡本身。
尽管如此,面对请愿,FDA 依然 10 年后才出台相关方案。当局绝不可能没有听到他们的呼声,但在当时,高危人群,尤其是男同性恋和静注吸毒者,早已被视为「可牺牲」的对象。同性恋进退两难:相较其他群体,他们面临的窘境 —— 既自我厌弃,又期待迷途中能邂逅真爱 —— 在这场当局者的态度模棱两可的「瘟疫」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至于医院的通宵煎熬取代了昔日舞厅内的夜夜笙歌,就更不值得一提了。
渐渐地,针对同性恋寻欢作乐的讥讽让位于了「同性恋只能听任死神摆布」的都市传说。只不过,讥讽也好,传说也罢,都(几乎)贴近真相。
戏剧《天使在美国》首版百老汇海报,该剧由 Tony Kushner 创作,在旧金山 Eureka Theatre Company 进行了首演,并于 1993 年来到纽约举办公演。
1981 年后,试图「讲述同性恋生存境况」的文艺作品都难免以偏概全。让我们把目光锁定在一部戏剧上 —— 由 Tony Kushner 创作,并于 1991 年问世的《天使在美国》(Angels in America,以下简称《天使》)。同样,《天使》不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关于同性艾滋病患者的戏剧(AIDS play),但却是首部「街头巷尾人人议论」的同性艾滋病患者剧。
《天使》中,同性恋依然拥有美好的未来,但狂欢的氛围一去不返:灾祸的意外到来,为他们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却阻挡不了他们对自由的追求和对性的渴望。《天使》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未对同性恋的寻欢之举进行尖锐批判,而是赞美同性恋的情感,歌颂他们「女王」般的气场 —— 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和社会阶层。在这里,无人彻夜起舞,也无人津津乐道于餐桌八卦。《天使》营造的火岛,是另一颗星球上的世外桃源。
剧中主人公遭遇的不止是自我毁灭与外界对同性恋的恐惧,更有本性、爱情、失恋时的心碎、苛刻无情的宗教、麻木不仁的政客、种族主义和阶级歧视。当然,还有比里根或 FDA 更加冷酷致命的病毒 —— 这里,我们暂且不过分剧透。
讽刺的是,《Dancer》以主人公之死收场,《天使》则让生活继续。
让我们仔细梳理这持续上演中的同性故事:穿过 1978 年男同性恋者自我毁灭的宏大叙事,跃入 1981 年的虫洞,来到 1991 年,最终,得以见证了一首拒绝毁灭的同性史诗。
故事就是一种见证,见证历史,也记录历史。以今天的眼光来看,《Dancer》的悲剧性足以让其他同类作品难以望其项背,这或许是作者始料未及的。人们可能只想知道,倘若眺望远方,能看见头戴方巾的士兵已经爬上骷髅马的马背,哪怕只是一瞥,那么,老去的年华、衰竭的肉身是否便不会如此沉重。
因为,即便艾滋病疫情肆虐八方,也没有什么能改变青春易逝的事实。狂欢终究会归于尘土,或随洒落的红酒消散。我们也依然珍惜这一切。
幸运的是,美好从未离场。从《Dancer》到《天使》,始终如一。《天使》的最后几句台词来自顽强生活的艾滋病患者 Prior Walter,他对观众如此道来:「你是美妙的生物,人人皆是。祝愿你:生命绵长。生命伊始,一往直前。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
川公网安备 51190202000048号
投稿交流: